社区企业初探
|
寇威威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面对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在提供公共服务时存在的失灵问题和复杂性社会议题的挑战,社区企业作为一种新的公共服务模式,基于公民和社区,运用商业化手段,追求社区的公共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改善社区公共服务、缓解社区贫困、增强社区凝聚力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界定社区企业的概念,了解其兴起的原因和背景,探索其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作用和意义,为促进其在我国的本土化发展奠定基础。 关键词:社区企业;公共服务;创新 公共服务创新作为一项重要议题,受到国内外学者和治理主体的广泛研究(Chen,Walker and Sawhney ,2019)。近年来,随着贫困、老龄化、环境、气候变化等复杂性社会议题的出现以及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面对的诸多困境,公共服务领域发生了剧烈变化(Needham, 2008;Pollitt ,2013)。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提供公共服务时所存在的“三重失灵”,凸显了仅靠单个主体内部的创新,有着巨大的局限性(Sinclair,Mazzei and Baglioni et al.,2018;Salamon,2003),更多的重点被放在了组织间交叉领域的探索和研究(Geuijen, Moore and Cederquist et al.,2017)。此外,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西方福利国家长期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政府在提供社会福利供给方面的垄断地位受到了挑战,重塑了政府、企业、公众、非营利组织间的关系,组织间的界限逐渐模糊。社区和个人越来越被鼓励参与到社会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以合作生产、公民社会、自组织等形式为社区提供公共服务。社区企业作为一种基于公民和社区的公共服务创新,在社区发展运动中取得了令世瞩目的成就,在西方福利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得到了广泛应用(Varady, Kleinhans and Van Ham,2015)。对于国内在社区企业研究方面的不足,亟需界定什么是社区企业?了解其兴起的原因以及作为一种公共服务创新,有何作用和功能?本文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社区企业的界定 社区企业起源于社区发展运动,由于其在社区重建和可续发展方面成效显著,为社区的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实现提供重要路径,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运用。社区企业的发展受其所处的社会、空间以及制度等环境的影响,学界对于社区企业的界定,也尚未形成统一的定论。 企业家精神在提高社区的经济和创新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塞尔斯基和史密斯 (1994)运用“社区企业家精神(community entrepreneurship)”一词来描述非营利组织中创业者的领导行为。社区企业指的是社区作为企业家,为了满足社区的需求,追求公共利益,通过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进行重新组合的结果(Vestrum,Rasmussen and Carter,2017),在此,社区企业既是创业活动的发起者,同时也是创业的结果(Peredo and Chrisman, 2006;Somerville and McElwee,2011)。英国发展信托协会对社区企业给出了明确界定:“社区企业组织通过经济、环境、文化和社会活动,致力于社区的可持续再生。它们是独立的、非盈利的组织,对当地负责,致力于让当地人参与到重建过程中来(DTA,2000)。”贝利(2012) 则采用间接的界定方法,认为社区企业是社会企业的一种特殊情况(Spear, Cornforth and Aiken, 2009;Pierre, Von Friedrichs and Wincent.,2014),即通过商业运营来维持其完成社会使命(Battilana and Dorado,2010)。但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社区企业把其社会价值创造限定在特定的人口或特定区域的人群,强调社区成员对于公共服务生产和供给的参与。除了地理区域的限制外,与社会企业有着相同的定义(Bailey, Kleinhans and Lindbergh ,2018)。 以上对于社区企业的定义虽然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方法,但是却具有相同的基本内核。首先,社区企业必须根植于社区。社区的发展具有很大的连续性,社区企业作为社会企业的重要子集,由社区成员或居住在特定区域的人建立,必须遵循社区发展的历史路径。如:矿区、山林等社区成员,由于传统的开采矿物,伐木工作,成为社区成员所具有的基本技能(Wang ,Huang and Hu,2017)。同时,社区的发展也应基于矿物和山林的现实社区背景,实现最大程度的社区参与。其次,具有明确的社区目标,社区企业是由社区建立起来的,社区企业的使命理应为追求社区公共利益,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如社区企业结合自身优势,促进社区经济增长、缓解贫困、改善居住环境、提供就业培训等。第三,运用商业手段,传统的非营利组织的主要收入源于社会个人和组织的捐赠,这就造成了慈善不足和慈善家长制的问题。通过商业手段,能够减少对于外部资金的依赖,增强社区企业的自足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Battilana and Lee,2014)。第四,利润不用于分配。社区企业的盈余,一方面用于为社区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另一方面再投资于社区企业自身的发展,不用于个人的利润分配(Van Meerkerk, Kleinhans and Molenveld ,2018)。 综合社区企业相关文献及以上基本核心的论述,本文将社区企业界定为:社区企业是基于社区资源,通过最大化的社区参与,运用商业化手段,实现社区公共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的混合型组织。 二、社区企业兴起的原因 (一)市场失灵 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分析框架,市场失灵指的是通过市场机制,无法有效的进行资源的分配和生产,尤其是在公共物品或服务的生产和供给过程中,不能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Sinclair, Mazzei and Baglioni et al.,2018)。 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效益的非分割性,每个人对该物品的消费,不影响他人的使用,但是很难通过技术或者收费的手段将任何一个人排除出去(Samuelson,1954)。然而,营利性组织的目标是使组织的利益最大化,通过市场机制,向顾客提供商品或服务,从而获得顾客的忠诚度,来确保在长期内最大化组织的财富。这就使得私营部门在公共物品或服务的生产和供给过程,导致外部性问题的出现:一方面,在提供教育、国防等的公共物品或服务时,一个人对该物品的的消费中受益,并不能采取有效手段阻止其他人从该物品或服务中受益,从而导致“搭便车”现象的出现,即在从该物品或服务中受益,而不承担成本。常常造成因其无法在短期内获得满足成本的回报而选择退出,使得公共物品或服务的提供远远低于社会效率。另一方面,营利组织在公共物品或服务的供给过程中,出于自利行为,往往忽视了负外部效应,如工厂污染,工厂在生产过程中,对周边居民的利益造成损害,却未承担任何成本,周边居民也未从中受到补偿,这使得政府干预成为必要。 (二)政府失灵 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过程中,有着其自身优势。其主要收入来源于税收,决定其目标是为了完成自身的政治使命,满足公民需求(Moore,2000; Herranz, Council and McKay,2011)。政府的干预有效纠正了市场失灵所导致的外部性以及公共物品或服务效率低于社会效率的问题。但其自身也会存在失灵,即政府的活动,并不总是那么“有效”。政府在公共物品或服务的供给过程中,政府不能像私营部门那样通过利润等指标来衡量对于公共价值的创造。对于组织内部缺乏绩效考核,从而来进行有效的监督。政府的目标和使命决定了其在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的过程中,可以不考虑效率和成本,使得政府机构臃肿、效率低下,造成资源的浪费。此外,政府作为“行政人”要求了政府人员一方面是在权力范围内,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是追求与公共权力相匹配的的道德价值追求。出于对两种利益追求的平衡,政府往往选择生产周期短、有利于提升政府影响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导致政府供给与公众需求存在偏差,无法有效达到公众的期望。 (三)志愿失灵 非营利组织作为“第三”部门,在弥补政府和市场在公共物品和服务供给过程中的不足的同时,也有其自身的问题和缺陷,也会像政府和市场一样存在志愿失灵。萨拉蒙(2003)认为志愿失灵主要体现在慈善不足、慈善特殊主义、慈善家长制、和慈善业余性。 慈善不足指的是,每个人都想在不支付费用的情况下,享受社会利益,即“免费搭车者”问题。相对于政府部门来说,仅仅依靠社会捐赠获得收入,难以提供社会理想的公共物品或服务。另外,在面对经济危机等制度性社会问题时,非营利组织发挥的作用有限。慈善的特殊主义,虽然,特殊主义作为志愿组织所具有的的优势之一,其成立往往有着其更为具体的使命、服务对象和人群,比如残疾人、失业人员等,能够把具有共同利益追求的特殊群体组织在一起。但也会因其对特殊人群的关注,使对该物品或服务有需要的人群被排除在外。慈善家长制,非营利组织的收入来源决定了其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是为了满足捐赠者所期望的社会需求的实现。捐赠者左右了非营利组织提供服务的类型和规模,缺乏对社会的回应性,难以实现有限资源的有效配置。慈善业余性,慈善组织受资金限制,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往往依赖志愿者的参与,缺少专业的人员的雇佣,很难像企业那样追求服务的质量。 (四)公民和社区创业的兴起 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反映了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整个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Gofen,2015)。随着外在背景的变化,公共服务经历了由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治理以及更新的治理理念和范式的转变。公众的角色也从被动转为主动,经历了被动的政策接受者、消费者、共同生产者、政策制定的参与者到创业者(entrepreneurs)的转变(Gofen,2015;Hartley, Sørensen and Torfing,2013)。在传统的公共行政时期,政府被视为执行政治决定的中立机构,在公共物品或服务的供给过程中具有垄断地位,认为“大而全”的政府可以满足公众的所有需求,这也导致了福利国家的出现。公民被视为政策对象,被动的接受国家的照顾。新公共管理时期,为了解决政府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问题,公共部门内部进行市场化的机构改革,公民被视为消费者,在不同的服务间进行选择(Voorberg,2017)。虽然单一的公共服务提供者会优先考虑公民的偏好,但公民仍被认为是被动的对公共部门的决策作出反应。新公共治理时期,公民作为共同生产者,政策制定的参与者,由被动的角色转为主动,参与到公共服务的供给过程中,通过参与政策制定过程来创造公共价值(Brandsen and Honingh,2016)。近年来,对于现有公共服务的不满,公民和社区愈发倾向于作为创业者,提供替代性的公共服务。 (五)抗解性问题(wicked problems)的出现 抗解性问题指的是存在知识不确定性和价值冲突的问题(Klijn and Koppenjan,2015)。首先,与驯服性技术问题(tamed technical problems)不同,通过增加问题的相关信息以及专家参与的传统技术方法难以取得成效。其次,抗解性问题的本质无法进行界定。一方面,每个抗解性问题都是新的挑战,缺乏对该类问题的科学知识和信息,无法厘清问题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于问题有不同的认知,甚至是相互冲突的,难以触碰到问题的实质。第三,抗解性问题具有不确定性,问题的发展是非线性的,很难预测问题发生的结果和概率。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又会引发另一个问题。无法解决,而又不得不去解决,这就促使政府部门经常处于创新状态。随着老龄化、环境保护、气候变暖等抗解性问题的出现,传统的由公共部门内部进行的创新暴露出在治理知识和技术上的不足,越来越需要注重政府、企业、社区、非营利组织等的合作创新,形成良好的公共服务组织生态。 三、社区企业的功能和作用 (一)改善社区公共服务 受经济危机影响,政府长期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使的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方面有所减弱。为了弥补政府收缩留出的空白,社区企业作为一种公共服务创新在社区发展运动中受到了广泛关注(Powell, Gillett and Doherty,2019)。首先,在组织使命和目标上,社区企业融合了非营利组织的社会使命和企业的商业使命,通过商业化经营的手段,为可持续的满足社区的公共利益需求,提供了资金支持。有效弥补了企业的公共性不足以及非营利组织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第二,社区企业运作方式多样,既可以采取公共服务供给与商业运作相结合的方式,如,通过雇佣残疾人、失业人员等进行商品或服务的生产,进行再就业培训的同时,又能参与到社区企业的运作。也可以采用公共服务供给与商业运作相分离的形式,如雇佣专业的人员进行社区企业的商业运作,确保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在市场上的竞争力,通过获取的利润用于完成其社会使命。第三,在具体运作上,通过积极的公民参与,为社区企业的运作贡献时间、经验等。同时,少量专业人员的雇佣,确保组织能够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以及提供专业的公共服务。 (二)缓解社区贫困 社区企业被认为是激发贫困社区潜力的重要工具,在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贫困问题作为一项全球性议题,各国政府、国际组织都在积极参与对于贫困地区发展的干预。相对于家长式作风造成的减轻贫困努力与社区贫困之间的现实差距,社区企业对于缓解社区贫困主要体现在:一是使分散的社区资源凝聚起来,贫困社区通常是处在土地贫瘠、资源稀缺的环境,并且表现出碎片化、原子化的状态,面对与贫困、教育、医疗相关的公共服务问题,往往需要集体的努力去实现,社区企业依靠社区社会资本存量,通过家人、朋友、协会等社会关系网络,集中社区资源作为社区创业的起始资产(Kleinhans,2017)。二是充分调动社区成员的积极性,家长式的缓解贫困的方式,忽视了公民和地方的力量,形成了“等、靠、要”的被动思维,最终使各种援助、项目沦为慈善工作。社区企业充分关注社区的需求,特别是在其他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下,被忽略的弱势和边缘群体,通过参与商品的生产或供给过程。促进地方就业的同时,对公民的积极参与形成激励。三是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社区企业通过持续性的公共服务供给,改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吸引外来资本的投资。同时,社区企业的商业化运作,刺激了公民个人的创业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 社区作为一种居住在特定区域的人所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面对城市化的冲击,呈现分化的趋势。社区企业通过对社区资源重新组合的基础上,增加了人们对于社区的认同,提升了社区凝聚力,主要包括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供公共空间,英国社区企业以社区住房协会、社区信贷联合会、土地信托等形式,向社区公民提供了类似哈贝马斯所认为的公共领域机制(蔡禾,贺霞旭,2014)。通过这些公共空间,包括弱势和边缘群体在内的每个社区成员可以平等的进入,并进行不同意见和利益诉求的表达。二是提供公共话题,公共空间的提供只是为公民的参与提供了平台,如何让异质性的社区居民凝聚在一起,对社区产生认同呢?社区企业的社会使命是追求社区的公共利益,为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愿景,通过共同倡议、共同生产、参与决策过程的方式,激发公民的公共精神,影响了其他社区成员对于该话题的关注,形成对社区的认同。三是共同抵御风险,社会企业是融合了社会使命和商业使命的混合组织,也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风险(Jäger and Schröer,2014)。一方面,社区企业的开放环境,促进了信息、资金、人才等的流动,使社区通过不断的学习,增加社区的风险韧性,另一方面,社区企业通过紧密的社会关系,形成了风险共担的局面(肖芸,2019;李延伟,2018)。 四、结论 本文通过社区企业相关文献的研究,界定了社区企业是基于社区资源,通过最大化的社区参与,运用商业化手段,实现社区公共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的混合型组织。面对公共服务供给的“三重失灵”、公民和社区创业的兴起、以及抗解性问题的出现,社区企业在改善社区公共服务、缓解社区贫困、增强社区凝聚力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为现有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不足,提供一种创新的路径思考。 对于进一步的社区研究,应考虑以下问题。首先,公共部门面对社区企业形成的挑战,如何做出回应?社区企业的兴起,反映了公民对于现行的公共服务供给的不满,而寻求的一种创新或替代性选择,颠覆了传统的运行系统和制度。有些学者认为,社区企业的发展造成了政府与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种威胁和夺权行为,需要予以抵制。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区企业弥补了公共部门创新的不足,通过认同社区和公民行动来表现出公共部门对于公民的回应性。其次,全球化背景下,加速了公共服务创新的流动。社区企业兴起于英国、美国、荷兰,后被广泛应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于社区企业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各地的案例研究。影响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般性因素是什么?后续需要不断的实证数据的积累。最后,社区企业的使命漂移问题,相对于企业的使股东利益最大化的使命,非营利组织和政府部门为了获取捐赠者和选民的支持,在确定其使命时显得更为具体和稳定(Moore,2000)。社区企业融合了社会使命和商业使命,对于商业使命的追求,是否是使公共服务偏好于少数有影响力的群体?造成社会使命的漂移。如何保持两种使命之间的平衡,对于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形成挑战。 参考文献: [1]蔡禾,贺霞旭.城市社区异质性与社区凝聚力——以社区邻里关系为研究对象[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2). [2]肖芸.政策转移研究的流动性转向——从国家中心到比较城市[J].社会学研究,2019,34(03). [3]李延伟.创新技术采纳中的风险治理:分析框架与研究议程[J].学海,2018(2). [4]Ana María Peredo and James J. Chrisman. Toward a Theory of Community-Based Enterprise[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6,31(2). [5]Bailey N. The role, organisation and contribution of community enterprise to urban regeneration policy in the UK[J].Progress in Planning,2012,77(1). [6]Bailey N, Kleinhans R, Lindbergh J.An assessment of community-based social enterprise in three European countries[J].2018. [7]Battilana J, Lee M. Advancing research on hybrid organizing–Insights from the study of social enterprises[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2014,8(1). [8]Brandsen T, Honingh M. Distinguishing different types of coproduction: A conceptu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classical definitions[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6,76(3). [9]Chen J , Walker R M , Sawhney M . Public service innovation: a typology[J].Public Management Review,2019(6186). [10]Development Trusts Association (DTA).Annual report[R].London:Development Trusts Association,2000 [11]Geuijen K, Moore M, Cederquist A, et al. Creating public value in global wicked problems[J].Public Management Review,2017,19(5). [12]Gofen A. Citizens’entrepreneurial role in public service provision[J].Public Management Review,2015,17(3). [13]Hartley J, Sørensen E, Torfing J.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 viable alternative to market competition and organizational entrepreneurship[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13,73(6). [14]Herranz Jr J, Council L R, McKay B. Tri-value organization as a form of social enterprise:The case of Seattle’s FareStart[J].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2011,40(5). [15]Jäger U P, Schröer A. Integrated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A definition of hybrid organizations and a research agenda[J].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2014,25(5). [16]Kleinhans R. False promises of co-production in neighbourhood regeneration: the case of Dutch community enterprises[J].Public Management Review,2017,19(10). [17]Klijn E H, Koppenjan J. Governance networks in the public sector[M].Routledge,2015. [18]Moore M H. Managing for value: Organizational strategy in for-profit, nonprofit, and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J].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2000,29(1_suppl). [19]Needham C. Realising the potential of co-production: negotiating improvements in public services[J]. Social policy and society,2008,7(2). [20]Pierre A, von Friedrichs Y, Wincent J. Entrepreneurship in society: A review and definition of community-based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M]//Social entrepreneurship. Springer,Cham,2014. [21]Pollitt C. The evolving narratives of public management reform: 40 years of reform white papers in the UK[J].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2013,15(6). [22]Powell M, Gillett A, Doherty B. Sustainability in social enterprise: hybrid organizing in public services[J].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019,21(2). [23]Salamon L M. Voluntary failure theory correctly viewed[M].The study of the nonprofit enterprise. Springer, Boston,MA,2003. [24]Samuelson P A.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54. [25]Selsky J W, Smith A E. Community entrepreneurship: A framework for social change leadership[J].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1994,5(3-4). [26]Sinclair S, Mazzei M, Baglioni S, et al. Social innovation, social enterprise, and local public services: Undertaking transformation?[J].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 2018, 52(7). [27]Somerville P, McElwee G. Situating community enterprise: A theoretical exploration[J].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2011,23(5-6). [28]Spear R, Cornforth C, Aiken M. The governance challenges of social enterprises: evidence from a UK empirical study[J]. Annals of public and cooperative economics, 2009,80(2). [29]Van Meerkerk I, Kleinhans R, Molenveld A. Exploring the durability of community enterprises: A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J].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8, 96(4). [30]Varady D , Kleinhans R , Van Ham M . Community Entrepreneurship in Deprived Neighbourhoods: Comparing UK Community Enterprises with US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s[J]. Iza Discussion Papers,2015,29(22). [31]Vestrum I, Rasmussen E, Carter S. How nascent community enterprises build legitimacy in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s[J].Regional Studies,2017, 51(11). [32]Voorberg W. Co-Creation and Co-Production as a Strategy for Public Service Innovation: A study to their appropriateness in a public sector context[J].2017. [33]Wang J, Huang X, Hu K, et al. An exploration on corporate-community relationship in mining sector in China–Lessons from Yunnan Phosphate Chemical Group Co., Ltd[J]. Resources Policy,2017,5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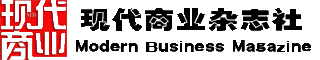


 网络经济下的工商
网络经济下的工商 国际货运代理企业
国际货运代理企业 家电企业营运资本
家电企业营运资本 基于开发维度对疫
基于开发维度对疫 A公司采购管理优
A公司采购管理优 高新技术企业研发
高新技术企业研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