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中国出口:一个文献综述
|
王于洋 上海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中国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环境问题,为改善环境,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以此为背景,环境规制与出口的关系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文章归纳分析了国内外关于环境规制影响出口的研究,阐述了环境规制影响出口的理论机制与实证效应。多数研究认为环境规制的实施能提高出口竞争力,并扩大出口量。已有文献为进一步研究二者的关系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但已有研究缺少对环境规制影响出口的动态效应分析,也未能妥善处理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 关键词:环境规制;出口;内生性 一、引言 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出口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货物贸易出口额由2000年2492.03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2.48万亿美元。然而,伴随经济高速增长和出口贸易规模扩大的是中国环境恶化问题越来越明显。《2018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8年,全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中,仅有121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占全部城市的35.8%。因此,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事实上,早在21世纪初,中国政府就制定和出台相关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实施排污收费制度和两控区政策等,更是在2013年实施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践表明,中国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就空气质量而言,2018年,全国PM10平均浓度为71微克/立方米,比2013年下降27%;首批实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74个城市PM2.5平均浓度为42微克/立方米,比2013年下降42%。 学术界对环境规制与出口之间的关系开展了详尽的研究。传统学派基于生产成本视角,认为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强增强了排污成本,由此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Van Beers et al., 1997)。但是有学者基于波特假说,认为环境管制能促进企业创新,由此产生的“创新补偿效应”可弥补排污成本,提升产品出口竞争力,扩大出口量(Melita, 2003)。综上可见,学界对环境规制对出口的影响仍未达成一致意见。本文归纳分析了环境规制影响出口的相关文献,试图理解并揭示环境规制对出口的理论机制与实证效果,探究争议的原因,并为政策制定者设计出能够持续改善空气污染的制度提供有力的依据。 二、关于环境管制影出口的理论研究 依不同的理论,环境管制影响出口的路径不一致。 有学者依据波特环境假说提出“创新补偿效应”,认为严格的环境管制会激励企业扩大研发创新规模(黄德春和刘志彪,2006),不仅可以提高产品质量与生产效率(王兵等,2008;李树等,2013),而且可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单位产品能耗(张三峰等,2011),由此产生的收益可以抵消环境管制强度增加引致的成本上升(Porter et al., 1995),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出口量增加(Melita, 2003)。 但反对者认为,依据污染天堂假说,环境管制会产生“出口成本效应”,即环境管制强度的增加会通过增加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而造成企业出口下降(Van Beers et al., 1997)。具体来说,环境管制强度的增加无疑会使企业增加生产技术投资以达到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何砚和陆文香,2019),譬如,购买减排设备、改进高污染生产技术线等,由此使得产品生产环境成本内部化(余东华和孙婷,2017),导致产品出口成本增加,不利于企业扩大出口量(Cole et al., 2005)。 除了以上结论,部分学者基于要素禀赋论,认为环境管制强度的增加对贸易影响不大,其原因在于相对于总成本,环境管制产生的成本效应极低(Levinson, 1995;许士春等,2009),而要素禀赋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环境政策差异对比较优势的影响(傅京燕和李丽莎,2010)。 三、关于环境管制影响企业出口的实证效应 实证研究的前提是对环关键变量进行界定与测度,因此,本部分首先总结和评价环境规制的测度方法,然后综述主要实证结果,并重点关注模型内生性问题。 (一)环境规制测度 就不同的研究层面学者采用了不同的环境管制测度方法。国家层面研究多采用环境诉讼案件数量、环保立法数量(Pargal和Mani,2000;Rennings和Rammer,2011;Barbu,2014),但环境立法并不能代表环境管制的有效实施。因此,有学者以制度实施结果来测算环境管制强度,譬如污染治理成本(董敏杰等,2011)、六类污染物加权求和(王国蒙等,2017)、染管制投资在工业总产出的占比(Lanoie et al., 2008)、工业环境效率(Yang and Li, 2019)、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工业废水排放标准率和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构建环境管制强度指标(Du and Li, 2020)、美国每天污水排放量除以我国每天污水排放量(王传宝和刘林奇,2009)等。 就行业层面,有学者采用实际污染排放数据,采用废水排放达标率、二氧化硫去除率、烟尘去除率、粉尘去除率和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衡量环境管制强度(傅京燕和李丽莎,2010)。事实上,实际污染排放程度决定于企业对污染的控制成本,从而影响其净出口,而净出口也会反过来影响污染排放,由此可能产生内生性问题(傅京燕和李丽莎,2010)。有学者采用污染排放治理费用率,即各行业废气和废水治理设施本年运行费用占行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景维民和张璐,2014)、废水废气年度运行费用和污染治理投资之和与行业总产值的比值(余东华和孙婷,2017)作为环境管制强度的替代变量。 基于企业微观行为,有学者采用问卷调查方式构建企业环境管制系数(Martín-Tapia et al., 2010)。然而,有研究表明这种主观测度方法容易产生响应误差(何文剑等,2019)。有学者基于企业行为的客观事实,采用企业一年内与环保部门打交道天数(童伟伟,2013)、政府环保检查次数(张三峰和卜茂亮,2011)、二氧化碳排放量(Richter and Schiersch, 2017; Forslid et al., 2018)、企业污染排放量(Levinson, 1996)等来构建企业环境管制变量。 考虑到制度测度难题,也有学者将地方环境立法作为准自然实验(李蕾蕾和盛丹,2017; Shi and Xu, 2018),譬如,两控区政策(盛丹和张慧玲,2017;Tang et al., 2020)、提高废水排放标准(Zhang yan et al., 2020)、提高排污费等(李卫兵和王鹏,2020)环境管制政策,采用双重差分(DID)或三重差分(DDD)等方法,识别环境管制对企业出口行为的效应。 (二)实证结果 基于国家层面,学者多认为环境管制会影响一国贸易。有学者对经合组织(OECD)国家研究发现,在实施严格的环境管制时,发展中国家的污染密集型产品出口仍然有所增加(Lucas and Hettige, 1992)。也有学者通过对日本1989-2003年41个产业回归发现环境管制是影响日本贸易的决定性因素,而且环境管制对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要大于发达国家(Cole et al., 2010)。对中国的研究中,学者们也多发现环境管制对中国制造业贸易部门有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尚在可承受范围内(董敏杰等,2011)。环境管制对我国比较优势的影响呈现“U”型,在拐点之前,环境管制对我国各行业的竞争优势呈现负面,而拐点之后则可以促进比较优势的形成(傅京燕和李丽莎,2010)。 基于企业层面的研究中,有学者发现环境管制带来的成本提高缓解了企业出口的增长(朱启荣,2007;Hering and Poncet, 2014)。通过对“提高废水排放标准”(Zhang et al., 2020)、 第十一个“五年计划”(Shi and Xu, 2018)政策的研究,发现严格的环境管制政策降低了企业出口的可能性与出口价值。而且,环境管制对污染密集型企业的影响更大(Du and Li, 2020)。然而,有学者发现“节能行动”这一环境管制政策对企业出口额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申萌等,2015),而两控区政策更可以通过提升企业产品转换行为相对地提升产品质量(韩超和桑瑞聪,2018) (三)内生性问题 内生性问题是现有研究存在广泛争议的原因。首先,模型中可能会遗漏同时影响环境管制与出口的变量,如企业特征和地区差异等。其次,环境管制与企业出口往往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具体来说,当企业出口规模增大时,对产品的需求量也会增大,排污量增大(Yang and Li, 2019)。那么,若采用实际排污数据测度环境管制变量时,便会产生双向因果问题。因此,有学者采用通风系数(Shi and Xu, 2018)、能源指标标准煤(傅京燕和李丽莎,2010)作为工具变量。也有学者将某一具体环境管制政策视为准自然实验,采用DID模型,试图解决遗漏变量或双向因果问题(Zhang et al., 2020)。 也有学者考虑了环境管制政策的自选择偏误问题(Self-selection Bais)。研究发现,某地实施环境管制某一具体政策的时间并非随即确定的,而是由政府依据当地污染程度、经济条件等综合作用的结果(申萌等,2015)。因此,部分研究采用了Heckman模型(Du and Li, 2020)或倾向匹配得分法(PSM)(申萌等,2015)来纠正自选择偏误。 四、总结 2001年加入WTO起,中国出口贸易高速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为此,中国实施了一系列环境规制政策,旨在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赢。基于此,学界对环境规制与出口的问题展开了详尽的研究,本文归纳分析了相关文献,理解并揭示环境规制对出口的理论机制与实证效果。这为进一步研究环境规制与出口关系的理论机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也为实证研究提供了相应的方法论指导。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与梳理发现,国内外对环境管制与出口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与实证层面展开了丰富的探讨,这为后续研究二者的关系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但仍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研究。首先,中国对已实施的环境规制政策不断进行调整,因此有必要研究其动态效应。譬如,在1982年中国政府便正式实施了排污收费制度,并在2003年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和完善,将SO2排污费的征收标准定位0.63元/千克。之后,部分地区主动将SO2 排污费从0.63 元/千克上调至1.26 元/千克。那么,环境规制政策的调整对出口效应的可持续性如何?可见,研究环境规制政策的出口动态效应十分必要。其次,多数计量分析未能科学识别并妥善处理模型中的环境规制可能存在的制度测度偏误、遗漏变量、自选择偏误及双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可能会造成估计结果的有偏。 参考文献: [1]Barbu E M, Dumontier P, Feleagă N, et al. Mandatory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s by companies complying with IASs/IFRSs: The cases of France, Germany, and the UK[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2014, 49(2): 231-247. [2]Cole M A, Elliott R J R, Okubo T. Trad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industrial mobility: An industry-level study of Japan[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0, 69(10): 1995-2002. [3]Cole,Robert, Shimamoto. Why the Grass is not Always Greener: the Competing Effects of Environment Regulations and Factor Intensities on US Specialization[J].Ecological Economics,2005(54) : 95-109. [4]Du W, Li M.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promoting the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Based on the dual margin of export enterprise[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0, 244: 118687. [5]Forslid R, Okubo T, Ulltveit-Moe K H. Why are firms that export cleaner? International trade, abatement and environmental emission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8, 91: 166-183. [6]Hering L, Poncet S.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exports: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4, 68(2): 296-318. [7]Lanoie P, Patry M, Lajeunesse 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productivity: testing the porter hypothesis[J].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 2008, 30(2): 121-128. [8]Levinson A.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manufacturers' location choices: Evidence from the Census of Manufactures[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6, 62(1-2): 5-29. [9]Lucas R E B, Wheeler D, Hettige H. Eco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f toxic industrial pollution, 1960-88[M].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1992. [10]Martín-Tapia I, Aragón-Correa J A, Rueda-Manzanares A. Environmental strategy and exports in medium, small and micro-enterprises[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0, 45(3): 266-275. [11]Melita M J.2003.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 - 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J]. Econometrica, 71(6) :1695-1725. [12]Pargal S, Mani M. Citizen activism,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he location of industrial plants: evidence from India[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00, 48(4): 829-846. [13]Porter M E, Van der Linde C. 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5, 9(4): 97-118. [14]Rennings K, Rammer C. The impact of regulation-driven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on innovation success and firm performance[J].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2011, 18(03): 255-283. [15]Richter P M, Schiersch A. CO2 emission intensity and exporting: Evidence from firm-level data[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17, 98: 373-391.、 [16]Shi X, Xu Z.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firm exports: Evidence from the eleventh Five-Year Plan in China[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8, 89: 187-200. [17]Tang H, Liu J, Wu J. The impact of command-and-contro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enterpris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China’s “Two Control Zone” policy[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0: 120011. [18]Van Beers C, Van Den Bergh J C J M. An empirical multi‐country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foreign trade flows[J]. Kyklos, 1997, 50(1): 29-46. [19]Yang X, Li C. Industrial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xport——Evidence from 30 provinces in China[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9, 212: 1490-1498. [20]Zhang Y, Cui J, Lu C. Doe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ffect firm exports? Evidence from wastewater discharge standard in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0: 101451. [21]董敏杰,梁泳梅,李钢.环境规制对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1(03):57-67. [22]傅京燕,李丽莎.环境规制、要素禀赋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J].管理世界,2010(10):87-98+187. [23]韩超,桑瑞聪.环境规制约束下的企业产品转换与产品质量提升[J].中国工业经济,2018(02):43-62. [24]何文剑,王于洋,江民星.集体林产权改革与森林资源变化研究综述[J].资源科学,2019,41(11):2083-2093. [25]何砚,陆文香.环境管制如何影响了中国企业的出口行为——基于企业融资异质性视角[J].财贸研究,2019,30(12):30-47. [26]黄德春,刘志彪.环境规制与企业自主创新——基于波特假设的企业竞争优势构建[J].中国工业经济,2006(03):100-106. [27]景维民,张璐.环境管制、对外开放与中国工业的绿色技术进步[J].经济研究,2014,49(09):34-47. [28]李蕾蕾,盛丹.地方环境立法与中国制造业的行业资源配置效率优化[J].中国工业经济,2018(07):136-154. [29]李树,陈刚.环境管制与生产率增长: 以APPCL2000 的修订为例[J].经济研究,2013(01):17 -31. [30]李卫兵,王鹏.提高排污费会抑制FDI流入吗?——基于PSM-DID方法的估计[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3):91-100. [31]申萌,曾燕萍,曲如晓.环境规制与企业出口:来自千家企业节能行动的微观证据[J].国际贸易问题,2015(08):43-50. [32]盛丹,张慧玲.环境管制与我国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基于两控区政策的考察[J].财贸经济,2017,38(08):80-97. [33]童伟伟.环境规制影响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吗?[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03):67-73+160. [34]王兵,吴延瑞,颜鹏飞.环境管制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APEC 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8(05):19-32. [35]王传宝,刘林奇.我国环境管制出口效应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9(06):83-90. [36]王国蒙,王元地,杨雪.环境管制对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的影响研究[J].软科学,2017,31(12):78-81+86. [37]许士春,何正霞,魏晓平.环境管制与企业国际竞争力:一个文献综述[J].商业研究,2009(09):34-37. [38]余东华,孙婷.环境规制、技能溢价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J].中国工业经济,2017(05):35-53. [39]张三峰,卜茂亮.环境规制、环保投入与中国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企业问卷数据的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11(02):129-146. [40]朱启荣.我国出口贸易与工业污染、环境规制关系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7(08):47-51+8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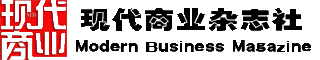


 “双循环”格局下
“双循环”格局下 中国肉类进口贸易
中国肉类进口贸易 SA8000标准对我国
SA8000标准对我国 数字贸易规则解析
数字贸易规则解析 数字贸易壁垒评价
数字贸易壁垒评价 品牌体验对贸易展
品牌体验对贸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