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Ӣ�����й�̨���������֯Ʒó�������ص�
|
����Ӣ����̨���������֯Ʒó�������ص㣨1961-1963�꣩ ����� ������ѧ��ʷѧԺ ������Ŀ������Ϊ���Ҽ���ѧ�����´�ҵ��Ŀ����Ŀ���ƣ�20����60���Ӣ����̨���������֯Ʒó���о�——��Ӣ���������ܵ���Ϊ���������201911258026�� ժҪ�����Ź�ҵ������չ������֯Ʒ��ΪӢ������Ҫ���ڲ�Ʒ����һս֮��Ӣ���������г��ij��ڱ������������֯��ҵ��˥�䡣Ӣ����ȡ���ִ�ʩ�����֯ҵ˥�����ƣ��ٴ�֮һ����1961�꿪ʼ���й�̨�������֯Ʒʵ��ó���ƣ������ȶ�������г����ڶ�������ս�ĸ��֮�£�Ӣ�����й�̨�������ó��������Ҫ���ǹ����г����������й���½���й�̨������ȶ���أ����ֽ������ص㡣 �ؼ��ʣ�Ӣ�����й�̨���������֯Ʒ��ó�����ߣ������� ����ҵ�����ǹ�ҵ������ҡ�����ܸ˺����壬���һ����ִ�������γɹ���������������ó�ס��Ե�һ�������ս��ԭ��ΪӢ����Ҫ������Ʒ����֯Ʒó��ʼ˥�䣬Ӣ����֯Ʒ��ӡ�ȵij��ڱ�սǰ�½���46%���Ժ�����ӡ��Ⱥ���½���55%�����й��½���59%��Ӣ����ҵ���壬1919��1939��䣬43%��Ӣ��֯������ʧ�ˣ�1926��1938��䣬41%��Ӣ��֯������ʧ�ˣ�1920����1939��䣬�����������½���45%��Ӣ��������1941��Ϊ��Ӧ��ս���������ӹ����������г�������ԭ�IJɹ��ͷ�����ս�������������������ڴ��ڼ�Ӣ������ԭ��ίԱ����Ӣ������Ψһ�����ߺͷ����̡�[1]��20����50���ĩ�������ͳɱ���Դ�Ľ���ʹӢ����֯ҵ�������ص�����״̬���������غ������Ŀ������˹���ʾ����Ҫ�����������Եͳɱ���Դ����֯Ʒʵʩ�������ơ�[2]����һ�����෴���ǣ�1961��ǰ�Ÿ��£��й�̨�������Ӣ������֯Ʒ���ڶ��1959��Ľ���������������ÿ��2900ƽ���롣[3]�ɴˣ��й�̨�������ΪӢ��������֯ҵ�����ж�����ȫ���ֳ��ֶ������Կ��ľ����£�Ӣ���������ڹ���ѹ������20����60������ڶ��й�̨���������֯Ʒ����ó�����һ�������߲����漰������֯Ʒ�г������漰�������й��ȶ�������뾭����ս���롣 ��Ŀǰ���о��ɹ�������ѧ�������սʱ�ڶ�����ó���Ƶ��о������Ǵ������ľ��ö������߿�ʼ�ģ�����������������ѧ����˹̹��ŵ�ġ����ö��ƣ���ͳ�붫����ó�����Ρ�[4]�����������˰���ͳ��ίԱ��Զ�����ó��Ӱ�죬�����ۼ��������ð�ͳ���й�ίԱ����й����о��ö��ơ�����ѧ�ߴ�ا�ġ���������սս�������ͳ��ίԱ�ᡢ�й�ͳ��ίԱ�ᣨ1945-1994����[5]Ҳ���о�������������������Ի�ó���Ƶľ���֮�������⣬�й�̨��ѧ������������������ս�е������ɣ�Ӣ����̨�����ߣ�1946-1958����[6]������ս��1958���ڼ�Ӣ�����й�̨����⽻���ߣ���ΪӢ�����й�̨�������ϲ�ȡ�������̬�ȡ����嵽��֯Ʒó���о�Ҳ��Ϊ�ḻ����˹��·�������ڡ����۹���һ���ʱ�����ȫ��ʷ��������Ϊ�������缶���÷�չ�����ǣ�����ȫ��ʷ�ĽǶ�Ϊ����㣬��Ϊ���۹�����ʷ��ij�̶ֳ��Ͼ���һ���ʱ����巢չ�����ŵ���ʷ��������������ȫ������ξ�������Ȼ�����۽���Ӣ�����й�̨�����ó�����ߵ�����о�����Խ��١����Ľ���Ӣ���������ܵ�������������Ӣ�����й�̨�������֯Ʒó�����ߵ����ݼ��ص㣬����Ӣ���ڸ��ӵĹ��ʻ������������߱����˼����Ȩ�⣬�����������ҹ���������һ�����н��вο������� һ�����ߵ����ݼ�Ŀ�� 1961����1963�꣬Ӣ��������������й�̨���������֯Ʒó�����ߡ���һ����֯Ʒó��������1961��11��16������������Ҫ����Ϊ���Ե�����Ӣ�����й�̨�������������֯Ʒʵʩ��������֤���ƣ���֯Ʒ���Ϊ1256��ƽ��Ӣ�ߣ�������Ϊ��1961��11��35����1962��6��30�ա�[7]1962��9�£�Ӣ������һ���߽����˵ڶ��ε�����������1963�꿪ʼ�����й�̨�������������֯Ʒ������245��ƽ��Ӣ�ߡ���Ȼ��Ӣ������ͬʱ��ʾ����һ���ֻ�漰����Ӣ���г��Ľ��ڷ�֯Ʒ�������й�̨��������ڵ�Ӣ�����мӹ������г��ڵ���������������������ɡ�[8] ��Ӣ���������ԣ��ȶ����ڷ�֯ҵ�г��ǵ�ǰ����������֮�ء��������������ս�ij����Ӣ�������������λ���䣬��Ϊ�������ҡ��ڹ������Ʒ��棬Ӣ������ʵ������˥�䣬���������Ʋ���սʱ���ü������ƽʱ�ڹ��ɣ���������ؽ���ȼã��ⲿ���Ʒ��棬������ӿ��ֳ����������˶������Ӣ�۹��ĸ�������ˣ�Ӣ���붫����ó���ܵ��������θ�ֵ����ơ�Ӣ�����й�̨�������֯ҵʵ��ó���Ƶ�ֱ��ԭ����Դ�Թ��ڷ�֯��ҵ��ѹ����1960�꣬��֯Ʒ�������������ӣ�����������صĽ��ڲ�Ʒ�糱ˮ��ӿ�룬����Ҳ��������֮ǰδ�������Ƿ�֯Ʒ���ڷ��Ĺ��ң���Щ���ڲ�Ʒ����������г���һֱ���Ŵ������������δ����IJ��˿�棬���ڷ�֯ҵ��1961��ĵ���״�����ںܴ�̶�����1960���������͵Ľ����1961�����ڽ���ͬ��������һ�����Ѿ������½������ڷ�֯ҵ���ţ�������Խ��ڼ������ƣ���ô����������������ʱ������������֯Ʒ��������ʽ�����֯Ʒ�������ҵľ��������չ��ڷ�֯ҵ�����ܵ����صij����Ӣ������Ϊ���ȶ������г������й�̨�������֯ҵʵ��ó���ơ�Ӣ�������ȶ����ڷ�֯ҵ��������Ϊ�������й�̨�������֯Ʒ��Ӣ���ij��ڣ������������������ơ�Ӣ�����⽻���ļ��ж���ᵽӢ�����й�̨���������֯Ʒó���ƵĶ������й�̨�������������“���⣬���й�̨��������ڵ����ڼӹ����ٳ��ڵ��������������ơ�”[9]������ָ֯�ɺ�û�о���ӡȾ�ӹ��IJ�������֯���Ʒ��Ӣ������֯��ҵ�����ɱ�������������ԭ�۸����������������Ƶ�Ͷ�룬��ӯ�������������ش�Ӱ�졣Ӣ���������й�̨������������ڣ����������ֶ�DZ��Ĭ����Ӱ���й�̨�������֯ҵ���г����ʱ����������ԣ���֯Ʒ���۳�·��խ������չ������ҵ������ͼ����ô�ʱ���Ȼ������������ҵ�������������й�̨������������Ӣ����������Ҫ�ṩ�̣�ΪӢ������֯ҵ�ṩ���۵���֯���Ʒ�������Ӣ����֯ҵ��ӯ�������� �������ߵ��ص� ����������Ӣ�����й�̨���������֯Ʒó�����߳��ֳ������Ե��ص㣬������������Ӣ�����й�̨�������������֯Ʒ���������ϡ�1961��11����1962��6�£�Ӣ�����й�̨�������֯Ʒ���Ϊ1256��ƽ���룬1963������й�̨�������֯Ʒ���Ϊ245��ƽ��Ӣ�ߣ��������ٵ����ƣ�������������й�̨���������˰��ó����Э�����й���½�������ķ��Ĺ��ǡ� ���й�̨������ĽǶ���˵���й�̨�������Ϊ��ó���Ƶ�“������”�����ò�˵�������ܵ�������һ����Ҳ�DZ��������ٵ�һ����ͻ��������ó���Ƹ��й�̨���������֯Ʒ�г������˲�С�ij�����й�̨�����������Ӣ����ѯʵ������Ƶ�ԭ����Ӣ�����¿��Ƕ��й�̨�������֯Ʒó�������ˡ�[10]Ӣ����������˶��й�̨�������֯Ʒʵ�����ı�Ҫ���Լ���Ҫ�ԣ���ӡ�ȡ��ͻ�˹̹��Ӣ������ҵķ�֯ҵ��Ը�����������Ӣ���ij�������̨ʵ��ó������Ϊ�����ض����������ķ�֯Ʒ��Ӧ�̡�[11]����Ӣ�����ڷ�֯ҵ��һ��˥����Ӣ�����й�̨�������֯ҵ�ĵڶ������Ҳ��1962��9��29��������Ӣ������Ԥ������һ�μ�С������й�̨��������Ŀ��飬����Ӣ����̨���Ŀ��鲻��Ϊ�⣬�������Ľ���Ϊ���������Ŀ�������������Ӣ���⽻���ļ���Ӣ�����й�̨������ĵ籨�����п��Կ����й�̨���������Ӣ���IJ���������ȫ�����·�ģ�Ӣ�����й�̨�������һ��֪ͨ�뱻֪ͨ�����������صĹ�ϵ���ɴ˿ɼ������ܻع������½���й�̨������ڹ�������������Եõ����صġ� �ӹ�ó��Э���Ƕ���˵������ƺ�����֤�ƶ��������������ƵĴ�ʩ����ó��Э����ԭ�����ǽ�ֹ����ƺ�����֤�ƶȵġ���ó��Э����11����1��涨��“�κε�Լ�������վ�˰�����������⣬����������ά��������������֤��������ʩ�����ƻ��ֹ������Լ�������IJ�Ʒ�����ˣ�����������Լ��������������۳��ڲ�Ʒ”��Ӣ���˾���ȻΥ���˹�ó��Э���Ĺ涨������1950��3���Ժ��й�̨������˳���Э�����Թ۲�Ա������ϯ��Э�����飬�й�̨������Ƿ����ڹ�ó��Э����Χ�ڵĵ�����һ���ͱ��ģ������������Ӣ���⽻���ļ����أ�Ӣ��������й�̨�����“û�й�ó��Э������������”��Ӣ������Ϊ�й�̨������������ڹ�ó��Э����Χ֮�ڣ������ӹ�ó��Э���Ĺ涨����ˣ��ڵ���ι�ó��Э���������߾��е�ó��̸�н����ã�Ӣ���Ͷ��й�̨������´����������ᵽ����֯Ʒó�����ߣ����й�̨����֯Ʒʵʩ����Ƶ�һ��ʱ����Ӣ����Ϊ�ܵ���ó��Э�������ƣ���˿�չ�˵ڶ��ε����ơ���һ����Ҳ��ӳ�˹�ó��Э�������Ա���ܿ����Ȳ��㡣 ���й���½���濴��Ӣ���ڶԻ������Ϸ���ҡ�ں���ԥ���������й�̨�����ʵʩ��ó�������߳ʽ������ص㡣�й���Ӣ����Ҫ�ij��ڹ���Ӣ�����й�������Χ�д�Ƭ������Χ���ر�����۵������Dz�������ʧ��[12]1954����������֮����Ӣ��ϵȡ�ýϴ��չ�����������������ƶ�˫��ó�����������ǣ�����������ֲ����ɶԻ�ʵ������“����������”����ʹ��Ӣó����Ȼ�������ơ��ڹ��̽�ͷ��Ե���ǿ��ѹ���£�Ӣ����1957��������������ӣ������������ſ��Ի�ó���ƣ�Ϊ��Ӣó�ķ�չ�ؿ��˵�·��1957���й���������Ӣ������ʱ����Ӣ������ǩ���˼�ֵ��70��Ӣ���ķ�֯�����Ľ��ں�ͬ����ó��������ָ�����й�������ó�ף�����Ϊ���ģ�Ҫ��������ݵ㡣��Ȼ20����50����������Ӣ���ó��չ̬�ƽϺã������й�̨������ʼ������Ӣ��ϵ���һ���̣�Ӣ�����й�̨�����ʵʩó��������Ȼ�Ʋ����й�������̬�ȡ���1961���Ӣ���⽻���ļ���Ӣ�����¹ݱ�ʾ��“�л��������ܶ�Ӣ����˾���й�̨���������ҵ��൱����” [13]�����ֳ�Ӣ���������й���½��ϵ�����ӡ�Ӣ�����й�̨�������֯Ʒ�������ʵ�н����ݼ�ʵ������һ����̽����̽��һ�ٴ���Ӱ�쵽�����й��Ĺ�ϵ��20����60������й���½æ�ڶ���ƻ����������ķ��ڹ��ҽ����ϡ�Ӣ�����й�̨�������֯Ʒ�䲼ó���������й�����������С�����˳����չ�ڶ��ε�������ơ� ����������������20����60�����̨��Σ��������Ӣ�����й�̨������ľ������ߵ��ƶ���������Ӱ��������Ӣ��������ʵ�����⽻��ͳ����һ���dz�������ҵ����Ĺ��ң������ߵ����Թ�������Ϊ�������ڶ���̨��Σ������ʱ��Ӣ���Ķ�̨������ƫ���������ڶ���̨��Σ������ʱ��Ӣ��ϣ����һ��̨��Σ��������Զ�������ĺ�ƽ�����ܹ�����άϵ�����ͬʱ��Ϊ������ʿ�˺�Σ����“Ӣ�������ϵ”���γɵ��˺���Ӣ���ֲ��ò�����������̨��Σ�������ϵ����ߡ����������������ʵ�������֧�֡�[14]Ӣ�����⽻���ļ��������ᵽ“������ô����۵��������Ǿ���ô���й�̨�����”��������˵��һ��������Ϊ��“��ȡ�������й�̨�������֯ҵ���ڵ���Ͼ����������������������۾����Ĺ��ʷ�֯ҵЭ����ì��”���������������Ҷ�Ӣ������ǰ��������������۷�֯ҵ��������Ϊ�Լ����ñ��ij��룬�����“�ܹ���������˵����ȡ��һЩ����”����һ������Ϊ�˱���������۵����棬“������ǵ������̨��ʩ�ӷ�֯Ʒ���ƣ�������������������������۽��ڵķ�֯Ʒ�������ܿ���������������������ı���������”[15]�������Ρ��⽻�����õȶ����Ŀ�����Ӣ�����ƶ����й�̨�����ó������ʱ�����ò�������̬�����뿼�Ƿ�Χ֮�ڣ���̨��֯Ʒ������СҲ����Ӣ������Ȩ��֮��ķ����� ������ʾ Ӣ����1961������й�̨�������֯Ʒʵ��ó����ʵ�����DZ�����Ӣ��������֯ҵ���������֮�١�Ӣ��������֯ҵ��˥�����Dz�������ʵ��1963��12����������ó��Э��������¥����������19������װ����ڰ칫�ҵ�“���ؾ��ֲ��Ҿ�”��һ����ǰ�����ֻ�����������ٵij���֮һ��������������������������ֲ����ŷ���������Լ�ȫ�������ߵ���Ҫ��Ŧ�����ǵ�1963�꣬ŷ�����۹���ͳ�ν����ˡ���20����60���ĩ��Ӣ��ֻ��ռȫ�������ڵ�2.8%����֯��������ɷ�֯����ݣ�����ֲ����������γ�������ŷ��֯ҵ����ó�ױ�������������ʱ����������ӿ���й��ķ�֯����ȫ��������й����������죬�й��Ĺ���ӵ�������Ͻ�һ���ɴ����֯������������ԭ������43%��20����60���Ӣ��Ϊ����������֯ҵ���������Ҳδ�����Ӣ����֯ҵ�����ƣ�������ǿ����ҵĽ��ʹ����ֲ������ҵ������½�����չ�� ��ȫ��չ���ӽ�������Ӣ�����й�̨�������֯Ʒʵ��ó��������ʱ�������������۵ģ������˹�ƽ�����г�������ȫ��������̵Ľ��죬�����һ����֮��ı˴���������ǿ��Ӣ���ȹ�����ó�ױ������壬�Ѿ��÷��������ƿص����ģ����������ҵ���ʵ��ó���ƣ�����ȫ��������ģ��DZ�Ȼ��ȫ���˳���û�ġ���Ϊ���ǵ���������Ӧ��ά��ȫ������ó����ϵ�Ϳ����Ծ�����ϵ���������ǿ������������Ӯ�������ֽ��ھ�����˹��Ϊ��19����������Ӣ���ģ�20���������������ģ�����21���ͽ��������й��ġ���Ϊ��ʱ����һֻ��Ҫ�������й�Ӧ����ȡӢ���Ľ�ѵ��ά��ȫ������ó����ϵ�Ϳ����Ծ�����ϵ���������ǿ������������Ӯ�� �ο����ף� [1]˹��·������.���۹���һ���ʱ�����ȫ��ʷ[M].�����,����,��.�����������뽨�������,2019. [2]From British Consulate to Tamsui, September 29, 1962, FCN1151/10, NO.1128, FO371-165119[A]. P61. [3]From Foreign Office to Tamsui, November 10, 1961, FCN1151/4, NO.97, FO371-158471[A]. P28. [4]Michael Mastanduno. Economic Containment: COCOM and the Politics of East-West Trade[M]. New York: Cornel University Press, 1992. [5]��ا.��������սս�������ͳ��ίԱ�ᡢ�й�ͳ��ίԱ�ᣨ1945-1994��[M].�������л����,2005. [6]����.��ս�е������ɣ�Ӣ����̨�����ߣ�1946-1958��[M].������,��.̨�壺��¹�Ļ���ҵ��˾,2014. [7]From Foreign Office to Tamsui November 10, 1961, FCN1151/4, NO.97, FO371-158471[A]. P28. [8]From British Consulate to Tamsui, September 29, 1962, FCN1151/10, NO.1128, FO371-165119[A]. P61. [9]From Draft Telegram to Tamsui, FO371-158471[A]. P23. [10]From Industrial & Coordination Group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to British Consulate, November 28, 1961, FO371-158471[A]. P38. [11]From British Consulate to Tamsui, December 13, 1961, NO1128, FO371-158471[A]. P39. [12]֣����,�����.����1949-1954��Ӣ���Ի����ߵ��ݱ估�䶯��[J].������ʷ,1995(06):2. [13]From British Consulate to Tamsui, May 22, 1961, FCN1151/3, NO.1128, FO371-158471[A]. P8. [14]������.�ڶ���̨��Σ����Ӣ���������⽻��Ӧ������[J].����ʷѧ,2019(04):114-123. [15]From Washington Telegram No.2855, October 27, 1961, FCN1151/4, FO371-158471[A]. P1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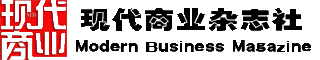


 ��˫ѭ���������
��˫ѭ��������� �й��������ó��
�й��������ó�� SA8000�����ҹ�
SA8000�����ҹ� ����ó�������
����ó������� ����ó�ױ�������
����ó�ױ������� Ʒ�������ó��չ
Ʒ�������ó��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