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GATT国民待遇原则相符性分析
|
蒋滨远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1620) 摘要:2024年欧盟颁布的《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下称“《指令》”),以 “可持续公司治理”为核心,要求价值链上企业承担环境、人权保护的义务。从立法动机看,《指令》的绿色目标下覆盖了复杂的利益诉求,一方面,目标本身是欧洲未来经济、政治力量崛起的重要一步。另一方面,具有道义色彩的绿色议题是欧洲保护本国企业、输出欧盟标准的工具。《指令》具有很强的域外性产生了贸易保护的嫌疑。通过分析发现,《指令》确实他国产品施加了歧视性影响,违反了国民待遇原则。我国应积极应对。揭露《指令》的贸易保护性质;结合国家战略,适度扩大绿色补贴范围;加快建立可持续披露制度。 关键词:尽职调查,企业社会责任,WTO法律制度 一、 引言 早在1916年,克拉克在其著作中就提出 “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这一概念要求在企业与利益相关者间构建一种新型秩序, 实现企业与利益相关者、自然环境、社会之间的持续健康发展。[1]由于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人权等议题的密切联系,在当下,人们又重新对其展开讨论。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试图借助这一概念来履行本国保护环境和人权的承诺。然而,人们也开始发现一些企业社会责任的举措超出了其应有的范围。一方面,某些国内政策通过与对外经贸法律工具紧密结合,将域外问题作为重要的治理目标。[2]另一方面,相应的保护措施往往会对贸易自由产生消极影响。基于上述理由,学者开始探讨这类带有价值取向的法令与国际法,特别是WTO法相符性的问题。 2024年欧盟颁布了《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下称《指令》)。该《指令》以 “可持续公司治理”为核心,通过强制企业披露ESG信息,直接要求企业对供应链中特定业务关系进行ESG风险自查自纠,规定企业损害赔偿责任[3]来实现监管目标。因为《指令》具有的强制性、涉外性,国内学者对CSDDD保持警惕。有学者就认为“CSDDD将强制让一些存在欧盟收入的第三国企业披露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报告,还将对存在欧盟地区合作方与客户的外国企业包括中国企业构成成本、管理、安全、供应链层面的风险”[4]更有学者将《指令》置于欧盟构建“规范性力量”的宏伟蓝图中考量,认为这正是“欧盟通过管辖范围内的法律实施,将特定的域外因素,如第三国的市场行为及效果、法律政策和治理水平等纳入欧盟法实施的考量范围,借此推动域外的行为、法律和治理结构同欧盟趋近,进而重塑跨国规则、国际法和全球治理格局”[5]的表现。 中国作为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一环,主导了全球价值链上下游中约一半的关键节点。[6]又与欧盟互为第二大的贸易伙伴。《指令》的出台势必会给中欧相关进出口贸易带来一定的影响。为此,本文将梳理《指令》的立法动机,剖析其制度逻辑;在此基础上,就CSDDD与现有的国际规则 (特别是WTO规则) 相符进行研究。并对我国相应的法治应对提出建议。 二、立法动机与制度逻辑 1..实现绿色目标的组成部分 《指令》是欧盟绿色协议(European Green Deal)的组成部分。欧洲绿色协议是欧盟为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实现碳中和[7]而制定的文件,协议以于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为核心目标。除气候治理议题外,其中还涵盖了如生物多样性、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循环经济等方面的内容,体现欧盟对绿色议题的高度重视。欧盟的主要国家领导人认为,绿色领域投入能够带来“显著的经济、安全和地缘政治利益”。绿色产业的发展不仅能够带动能源系统的转型升级,同时还将确保未来欧盟在绿色经济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进而带动制造业的转型振兴及就业岗位的持续增长。[8] 2.平衡企业负担,维持竞争优势 欧盟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下降是出台绿色产业政策的根源。近年来,欧洲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欧盟在全球经济中份额逐步下降。以购买力平价衡量,欧盟GDP占全球比重由2000年的23.5%下滑至2023年的14.7%。[9]为维持本土产业竞争力,欧盟更多利用投资与贸易保护工具和措施。为支持本国企业复兴,欧盟一方面利用区域内绿色行业和环保组织活跃,环保、节能和可再生能源丰富的优势,削弱原材料出口国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利用本国广阔的内部市场,帮助成员国企业获取世界市场。具体而言,欧盟通过其巨大的内部市场在经贸投资协定中提高要价,帮助欧盟成员国打开更多的市场,并推广欧盟的劳工、环境、数据流动等各方面的标准。[10] 3.输出欧盟标准,强化企业社会责任话语权 通过《指令》向全球输出欧盟标准。学界已对欧盟标准输出模式进行研究,主要总结为以下几种形式:一、引导欧盟价值观成为范式,影响他国国内法的内涵。金晶(2023)认为欧盟谋划通过宣言、条约、政策、标准、条件等规范性基础,传播欧盟价值原则,从而形成规范性概念[11],以这种“规范性概念”影响他国对国内法的理解。二、引领国际规则的塑造,间接影响他国规范。冯玉军,卫洪光(2023)认为欧盟立法模式的成功扩散,也体现在其对国际规则制定的超级影响力[12]上,国际条约的约束又带来了他国国内法的修正。三、规范力量不仅体现在立法的最终形成,在规范传播的过程中,也能带来国际地位提升等额外效果。[13]而上述这一系列输出路径都在CSDDD中有所体现。 除上述方式外,《指令》还通过司法救济渠道来达成重塑国际法的效果。首先,通过解释将欧洲价值融入国际法。《指令》内容具有较大的解释空间。如规范的第七条、第八条使用的 “适当措施”、“立即的可能”、“足够减轻”、“必要的”、“合理的”、“清晰的”、“有效的”,开放的“不直接商业关系”等用词,给予法官较大的解释空间。欧洲法院在救济外国企业时,以本国价值重塑了国际法。《指令》对本国企业施加负担,本国企业因价值链上的商业地位,将负担转嫁给依赖欧盟市场的外国企业。简言之,外国企业受到“长臂管辖”。在此基础上,外国企业若寻求欧盟法院,而非母国救济就会产生输出欧盟标准的效果。当事人寻求欧盟法院解释《指令》及《指令》中参引国际条约的内容。法院将通过有利于本国的方式解释国际条约。美国法院就有如此适用的先例。在Kiobel案中,法官将Alien Tort Stature的域外适用问题,解释成违反国际法进行追责,即通过转化--将国家间法律选择的问题,以“与国际法内涵重合”为由,转变成法院法解释的问题。[14] 其次,通过豁免将监管要求内化为企业日常管理内容。《指令》的“长臂管辖”表现为将欧盟公司面临的行政处罚通过合同关系转嫁给价值链,同时又允许豁免。豁免将形成示范,激励外国企业遵守欧盟法律。有学者就指出了,个案处罚威慑效应基础上的激励策略向非本国人传递了合规企业“少被罚”的“金色盾牌”,促使“非本国人”将单边经济法律规范内化为企业日常的合规要求,主动防止违反外国规范。[15] 第三,违反“意思自治”原则,强制司法管辖。“意思自治”是调整民事关系的基本原则,在国际私法中表现为当事人可以对合同适用的法律及管辖的法院进行选择。然而,《指令》的豁免内容限制了当事人选择的余地。其理由有三。一、外国企业在合同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合同更有可能约定由欧洲法院管辖。消费者市场不仅使欧盟在国际经贸规则的谈判中占据优势,欧洲企业也同样因此在合同谈判中占据主导地位,外国企业为达成合作,愿意接受《指令》规定的强制性条款。二、当事人出于成本、便利性、确定性等因素考虑,选择欧洲法院管辖更为合理。《指令》下的侵权请求权多由欧盟的自然人或组织行使。一方面,欧盟作为中心国家,具有相对丰富的产品需求。另一方面,欧洲的环保组织十分活跃,对环保议题积极的推动。在这种情况下,诉讼两造往往都是欧洲人,而本地法院是成本最低、最为方便的选择。不仅如此,由欧洲的法院管辖,在判决的内容和执行上更具确定性。豁免涉及解释的问题。类似于“刺破公司面纱”中的人格混同,法官在豁免的确定上具有较大自由裁量权。申言之,只有权利人证明公司具有主导子公司及价值链的能力,公司才需要对它们的行为负责。而在能力认定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以“刺破公司面纱”的实证研究为例,在不同地区,因法官对公司法的理解和认识不同,在面纱刺破率上就有很大差异。[16]进言之,这种差异在不同法律传统的国家间更甚,而导致判决不同或判决不被承认的后果。三、诉讼以欧洲企业为适格主体,排除价值链上其他国家管辖和法律适用的可能。《指令》规定以欧盟境内经营的本国或第三国企业为责任主体。[17]受损害的自然人或法人,只能对上述主体因故意或疏忽地不遵守第10条和第11条中规定的义务[18]提起诉讼。换言之,第三国企业作为独立的主体,并非适格的诉讼主体。《指令》第29条第一款规定“如果损害仅由其业务链中的业务合作伙伴造成,则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正是这个意思。侵权案件的管辖和法律适用,一般以损害发生地为连结点[19]。如果存在共同惯常居所地,则以此连结点优先。[20]在《指令》的侵权案件发生时,法官往往不会否认本院的管辖权及本国法适用的合理性,从而忽视其他国家管辖和法律适用的可能。事实上,欧陆法院在审理跨国公司注意义务的案件中,引入了必要法院原则,消除管辖权的障碍。[21] 从立法动机看,《指令》实际包含了复杂的利益追求。它的绿色目标实际覆盖了更加深层次的追求,一方面,绿色目标本身是为欧洲未来经济、政治力量崛起做的准备。另一方面,具有道义色彩的绿色议题,是欧洲向全球施加压力的工具。实际起到保护本国企业、输出欧盟标准的作用。 二、《指令》的合法性争辩 1.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违反WTO规则 《指令》具有保护本国企业的立法意图,存在违反WTO规则。《指令》调整外国企业的指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调整对象域外化。CSDDD的责任主体包括外国企业,具体有三种情形:(1)上一财年于欧盟境内取得净营业额超过4.5亿欧元的企业;(2)所在集团达到上述门槛的最终母公司;(3)在欧盟通过签订特许经营或许可协议确保共同的身份,特许权使用费在欧盟的金额超过 2250万欧元,并且该公司或集团的最终母公司在上财年于欧盟境内取得净营业额超过8000万欧元。[22]第三国企业也有可能成为其直接监管的对象。CSDDD将义务范围扩展到欧盟领域之外。依据指令第一条第一款,企业不仅要对自己的经营活动进行调查,还要对子公司以及通过价值链进行的活动进行评估。[23]二是责任承担的民事化。民事责任被视为是欧盟“长臂管辖”的一种手段。一般情况下,国家通过行政机构调查、起诉和扣押等强制力量对违法人员实施罚款、追究刑事责任等强制性处罚,保障环保等政策目标的实现。[15]这种方式的惩罚对于域外的对象的效果较差。《指令》则基于工商业领域的“共谋”理论与“注意义务”[5]发展出由业务往来对外国企业施压的模式。具体而言,企业与其子公司、直接或间接商业伙伴共同造成损害时,将按份承担共同责任。外国企业更容易因弱势的商业地位而屈服。三是责任后果的强制化。自出台《新版欧盟公司社会责任战略文件(2011—2014年)》始,欧盟就积极推动企业责任实施方式的转变。《指令》对公司的责任后果明确,如第20 条对行政处罚作原则规定;第7、8条则给予企业合同权利,作为消除和避免不利影响的手段,即相对方违反义务将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就是将原来的软法模式“硬法化”的表现。[24] 2.涉嫌违反GATT的国民待遇原则 《指令》具有涉外性,并不足以认定其违反WTO规则。是否歧视性削弱了外国企业相对与本国企业或第三国企业的竞争力,才是判断《指令》相符于WTO规则的重心。《指令》中增加企业主体负担的监管模式,常常被认为是由GATS或SCM调整的。实际上,尽职调查责任更应被视作是一种执法模式的转变,《指令》关注于价值链中的某一产品。换言之,《指令》同样有违反GATT中国民待遇原则的可能。 国民待遇原则体现在GATT第3条。参照WTO之前的判例,违反国民待遇一般需要满足四个构成要件。(一)属于同类产品。总体来看,判断同类产品的方法有以下三种,一是在1970年关于边境税调整案的报告中提出的“传统标准”,报告指出同类产品应当由个案的实际情况认定,并提供了认定的参考因素包括在既定市场上的产品最终用途;消费者的品味、喜好、习惯、对产品的认知及行为反应等;[25]二是1992年美国影响酒类及啤酒饮料措施案、1994年美国汽车税案提出依国内管辖权限的“目的与效果”来解决同类产品的问题。[26]这种方法关注差别待遇的来源,若系争措施具有保护某一产品的目的或效果,则不必局限于文义,即可认定两者为同类产品。三是在“中国出版物案”中形成的,起诉方可以通过证明系争措施仅根据产品的原产地给予差别待遇来确立“同类产品”。[27](二)属于第3.4条“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范围,(三)影响了“进口同类产品的销售、购买、运输、分销或使用”。专家组曾认为,“影响”不仅包括直接调整销售或购买条件的法律,还包括对进口产品的销售、标价出售、购买和使用“产生激励或抑制作用”的措施。[28](四)措施对进口产品给予“更低优惠的待遇”。具体而言,这包括两方面的要求:一是不应对特定成员的产品给予低于其他成员产品的更次待遇;二是不应对特定成员的商品给予优于其他成员产品的更优待遇,包括提供额外的市场准入机会,给予更优惠的竞争条件等。[29]是否造成实际损害在所不问。[30] 判断《指令》是否违反GATT的国民待遇原则,重点在认定产品与歧视这两者的关系。申言之,上述四个要件在判断中存在交错关系。认定同类产品,一方面取决于产品在物理性质上的相似性,另一方面又需要考察国内法特殊保护的意旨。在措施成立的判断上,同样存在“产生歧视效果的是措施,措施产生歧视效果”的循环。 《指令》违反了国民待遇原则。首先,措施对产品施加了影响。《指令》抽象地规定符合一定条件的全部企业均具有供应链尽职调查义务,表面上具有普遍适用的特征。[30]然而,价值链才是《指令》真正约束第三国企业的纽带,具体表现为对原材料、产品或产品部件的设计、提取、采购、制造、运输、储存和供应、产品或服务的开发以及与分销进行监管。[31]要求企业在价值链中履行尽职调查义务,实际上等同于对产品施以有关环境、人权保护等附加条件。 其次,《指令》对进口产品予以歧视。由于各国发展状况和能力的不同,基于“共同而有区别原则”不同国家国在立法程度上的差异是可以接受的。不同国家基础保护程度的参差造成了《指令》对各国产品影响程度的区别,产生了歧视。欧盟委员会工作报告(COMMISSION STAFF WORKING DOCUMENT)称“超过 90% 的首席执行官表示,可持续发展对其公司的成功至关重要,许多公司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并销售可持续产品或服务” 这也从侧面表现出企业社会责任在欧盟已有较高的普及,相应的管理模式也已较为完善。换言之,技术落后、依赖污染红利的外国企业将会受到更大的冲击。如果公司尽责法对进口产品的影响明显大于对本国产品的影响,那么公司尽责法可能导致对同类产品的差别待遇,被认定为对来自其他国家的产品构成间接歧视。 存在事实上的歧视。事实上的歧视是指欧盟企业基于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优势地位,在关键产业和产品上更具掌控力,相较于外国企业更能抵御断链的冲击。[32]使外围国家的企业因转嫁等原因实际上承担更重的负担。根据全球价值链理论,欧盟对全球价值链具有较强的俘获能力。俘获能力是跨国采购商对仅拥有劳动力资源等低级要素的国内代工企业的升级自主权进行控制的一种权力。这种能力的大小主要与对产品终端市场销售渠道、品牌和设计研发等价值链核心要素的控制有关。[33]欧盟在全球价值链上具有较强的俘获能力,造成外围国家企业即使在相同的规制下,也仍承担更重的负担。一方面,外围国家企业抵御外部性的能力较弱。外围国家是在国际分工格局中为大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的那一部分。[34]它们依赖于自然条件,发展原材料出口产业。这类产业以原材料开采为中心,在组织结构、技术水平以及企业策略调整上都不如以资本为主要投入的企业灵活。环境保护责任可能根本剥夺了企业发展的权利。另一方面,外围国家的企业更容易受到污染环境等谴责。2020世界发展报告就声称“形成规模的外围国家企业造成了更大的污染”[35]。事实上,这正是落实环境责任时发生的歧视。有学者就提出,基于“生产者责任原则”分摊环境责任容易导致造成“碳泄漏”(carbon leakage),弱化减排政策等效果,“消费者责任原则”(Consumer Responsibility Principle)消费侧碳核算方案,[36]可能是一种更公平的核算方法。 综上所述,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对产品施加了影响,并在本国产品与外国产品间产生差别待遇,可以认定《指令》违反了GATT中的国民待遇原则。 三、结语--CSDDD的中国因应 1.揭露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具有贸易保护性质 中国应在国际场合深刻揭露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所具有的贸易保护特质,取得其他受影响国与国际社会正义力量的支持,提升在国际谈判中的优势。通过欧盟《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与GATT国民待遇原则相符性的分析,可以基本确定《指令》损害了贸易自由,对外国企业予以歧视。欧盟基于提升自身国际政治和经济地位的立场,有意推动本国绿色产业转型升级。[37]同时,通过执法模式的转变,利用自身比较优势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特殊地位对外国产品在法律上、事实上歧视,极大约束和限制了外国企业的竞争力。 2.结合国家战略,适度扩大绿色补贴范围 与本国产业政策相结合,适度给予绿色补贴。一方面,我国应当在WTO中积极维护自己的权益。另一方面,也应当承认WTO的救济存在一定的缺陷和滞后性。败诉方不必赔偿过去的损害,报复和补偿。在赔偿时,通常不是受到无意的拖延,就是故意的藐视。[38]这种情况下,我国可以通过扩大绿色补贴的范围抵御短期风险。 给予企业补贴具有必要性。企业在短期内存在被拉跨的风险。受规制的企业往往属于资源或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因产品价格刚性及本身技术水平低下等因素影响,企业无法在短期内通过技术升级降低成本,可能在转型前就面临破产。 绿色补贴符合WTO规则。绿色补贴属于不可诉补贴。绿色补贴在构成上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是一次性、非重复的,是直接与企业减少废弃物和污染的计划有关的,是所有厂商均可得到的。同时,补贴还受到一定限制。补贴的给予不能产生节省制造成本的的效果,在数量上限于改进成本的20%。扩大绿色补贴范围是符合绿色补贴要求的。首先,尽职调查机制的核心就是为了减少废弃物和污染,企业为履行尽职调查义务所做的努力与环境保护的目标直接相关。其次,与欧盟存在贸易关系的企业都有动机和能力建立尽职调查机制,大部分企业都应当取得绿色补贴。第三,建立尽职调查机制,正是为了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机制,达到保护环境的效果。不仅加工工艺的成本,遵守《指令》的成本也应当视为改进成本。总之,我国可以适度宽泛的理解绿色补贴。在范围上对处于全球价值链上的企业均给予绿色补贴。在程度上,将企业为遵守《指令》可能付出的如诉讼成本、合规成本都计入改进成本的范围。 提供补贴应当适当,与本国产业政策相结合。第一,应当警惕过度补贴“僵尸企业”。经济学家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保证补贴准确十分困难。政府补贴因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面临扭曲性激励的风险。[39]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在政府补贴下存活,造成资源的浪费。进言之,补贴应当限定在正好抵消CSDDD的范围,留给企业足够的竞争环境。其次,补贴应与产业政策衔接。我国产业结构逐渐具备从传统加工产业向转变的更高端产业转型的条件,[40]国内也在积极推动产业升级。绿色补贴应避免与产业政策冲突,协调产生合力。针对《指令》的补贴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以吸收企业短期风险为目标,二是以式微的传统产业为政策对象。这类补贴可以与两类产业政策即绿色转型产业政策及衰退产业援助政策相协调。 绿色转型产业政策以解决外部性和系统失灵为目标。在外部性方面,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方式激励企业保护环境和技术改进,对消费者进行补贴,推动绿色消费市场。在系统失灵方面,提供软硬基础设施促进技术变革。[41]对于有转型可能的企业,在制定政策时可以以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形式,将《指令》内容与国内绿色目标统筹考虑,在产业发展前期给予绿色补贴。 衰退产业援助政策是针对衰退产业,以及产业衰退地区,政府所实施的一系列减轻社会摩擦、改善和提高社会生产率政策的总称。[42]这类产业政策的重点在扩大就业、维护社会稳定。[43]针对无转型可能的受规制企业,一方面,国内的“促退”政策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另一方面,减少针对《指令》补贴的投入,将资源集中在保证企业的平稳退出上。如建立产业救助机构协调产业退出行动,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保障衰退产业就业人员妥善安置。[44] (三)建立可持续披露制度 我国专门的可持续发展披露制度还不完善。国内已有许多企业将社会责任作为运营策略。国有企业也从侧面履行着企业社会责任。但在制度中仍缺少通过披露进行监管的方式。披露制度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都十分重要。在国家层面,本国的可持续披露标准有助于抵御欧盟不断扩张的规范力量。披露制度的建立,一方面需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如以联合国《全球契约》《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等国际文件为指引。另一方面,也需要表达自己的立场。经济主权原则和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原则都是国际经济法中的基本原则,它们允许发展中国家在承担责任时存在例外,与中国实际结合。 可持续披露标准的建立为中国在国际上发表意见提供了理论依据,有助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从微观层面,企业社会责任及披露制度的建立将优化市场环境。有学者就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可以降低企业内外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主并企业的企业声誉、降低主并企业管理者的自利程度,抑制绿色并购溢价。[45] 参考文献: [1]殷慧芬.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起源及其法律价值[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92-97. [2]Jan H.Jans and Hans H.B.Vedder.European Environmental Law (Third Edition)[M].Europa Law Publishing,2008. [3]赵爱玲.欧盟“新ESG法规”落地对中国绿色供应链建设提出挑战[J].中国对外贸易,2024(8):36-37. [4]姜冯安.欧盟ESG监管的双重路径及对华影响——可持续金融与可持续公司治理[J].欧洲研究,2024,42(3):139-162. [5]叶斌,杨昆灏.欧洲的权利经济转型——基于对欧洲公司可持续性尽责法的考察[J].欧洲研究,2022,40(6):76-107. [6]贾平凡.中国是推动全球价值链发展的重要力量[N].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4-05-06(010). [7]庄贵阳,朱仙丽.《欧洲绿色协议》:内涵、影响与借鉴意义[J].国际经济评论,2021(1):116-133. [8]杨成玉,董一凡.欧盟绿色产业政策及其对中欧经贸关系的影响[J].德国研究,2023,38(4):25-41. [9]李颖婷.欧洲提高竞争力的瓶颈与机遇[N].商广网.http://sqtv.net/news/bencandy.php?fid=148&id=253746 . [10]郑春荣,吴永德.欧盟产业政策调整及其对中欧合作的影响[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1):98-106. [11]金晶.欧盟的规则,全球的标准?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的“逐顶竞争”[J].中外法学,2023,35(01):46-65. [12]冯玉军,卫洪光.GDPR的“布鲁塞尔效应”理论及批判——对立法域外影响力的分析[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36(6):24-34. [13]王展鹏.全球治理视野下欧盟规范力量探析——以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权改革为例[J].欧洲研究,2011,29(1):57-71. [14]Kiobel v. Royal Dutch Petroleum Co., 569 U.S. 108 [Z].2013. [15]郭华春.美国经济制裁执法管辖“非美国人”之批判分析[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1,23(1):122-137. [16]马齐林.美国法院“刺破公司面纱”考量因素之实证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法治研究,2013(6):62-72. [17]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due diligence and amending Directive (EU) 2019/1937 and Regulation (EU) 2023/2859 Article 2.2 [DB/OL]. https://eur-lex.europa.eu/eli/dir/2024/1760/oj/eng. [18]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due diligence and amending Directive (EU) 2019/1937 and Regulation (EU) 2023/2859 Article 29.1 [DB/OL].https://eur-lex.europa.eu/eli/dir/2024/1760/oj/eng. [19]REGULATION (EU) No 1215/2012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rticle 7.2 [DB/OL]; REGULATION (EC) No 864/2007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Article4.1[DB/OL].https://eur-lex.europa.eu/eli/dir/2024/1760/oj/eng . [20]REGULATION (EC) No 864/2007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Article4.2[DB/OL].https://eur-lex.europa.eu/eli/dir/2024/1760/oj/eng . [21]王晓彤.工商业与人权的司法救济:域外实践与中国因应[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4,39(2):144-155. [22]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due diligence and amending Directive (EU) 2019/1937 and Regulation (EU) 2023/2859 Article2.2 [DB/OL]. https://eur-lex.europa.eu/eli/dir/2024/1760/oj/eng. [23]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due diligence and amending Directive (EU) 2019/1937 and Regulation(EU)2023/2859Article1.1[DB/OL].https://eur-lex.europa.eu/eli/dir/2024/1760/oj/eng . [24]何志鹏,王惠茹.国际法治下跨国公司问责机制探究——兼评国家中心责任模式的有限性[J].国际经济法学刊,2019(3):1-14. [25]石静霞.“同类产品”判定中的文化因素考量与中国文化贸易发展[J].中国法学,2012(3):50-62. [26]曾炜.探析关贸总协定中的“同类产品”[J].WTO经济导刊,2013(11):90-92. [27]刘晓豹.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的WTO合规性问题分析[J].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22,29(5):5-22. [28]陈卫东,黄芷蕙.美国清洁汽车税收抵免措施的WTO合规性:兼论新能源补贴规则改革的中国因应[J].经贸法律评论,2024(6):30-46. [29]佟占军.WTO反补贴规则与国民待遇原则的适用关系[J].经济经纬,2009(5):153-156. [30]沈伟,陈徐安黎.供应链尽职调查国内立法的国际法分析——以WTO规则为切入点[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4(6):135-153. [31]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due diligence and amending Directive (EU) 2019/1937 and Regulation(EU)2023/2859Article3.1[DB/OL].https://eur-lex.europa.eu/eli/dir/2024/1760/oj/eng . [32]European Commission,“Strategic Dependencies and Capacities,”Commission Staff Working Document,SWD(2021)352final[DB/OL].https://eur-lex.europa.eu/eli/dir/2024/1760/oj/eng . [33]许南,李建军.全球价值链研究新进展:俘获型网络的形成与突破对策[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40(1):75-79. [34]沈尤佳,陈若芳.全球产业链重塑:逻辑、目的与中国应对[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10):115-129. [35]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20 Trading for Development in the Ag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J].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server/api/core/bitstreams/07eb7f0e-03b1-5a5d-924e-c0d40f95e678/content . [36]卫瑞,彭水军,张文城.全球价值链中的碳排放责任分担:基于价值俘获视角[J].国际经贸探索,2022,38(10):37-51. [37]董一凡,赵宏图.欧盟绿色产业新政的雄心及困境[J].和平与发展,2023(5):102-127. [38]余敏友.论世贸组织法律救济的特性[J].现代法学,2006(6):14-24. [39]徐震,黄健柏,郭尧琦.政府补贴、企业属性与过度投资——基于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2(1):73-84. [40]林毅夫,陈超然,付才辉.新质生产力理论: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J].学术论坛,2025,48(1):1-12. [41]徐雅卿,沈开艳.全球价值链重构下产业政策的多元化目标取向:一个理论分析框架[J].经济学家,2024(4):78-87. [42]尹小平,栾天野.日本产业调整援助政策研究[J].学习与探索,2023(4):138-144. [43]陈婉玲.衰退产业财政援助政策的法律保障——以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为背景[J].法学,2010(11):3-11. [44]黄征学,滕飞,高钬.我国产业衰退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点及思路[J].经济纵横,2018(11):96-102. [45]邱菊,薛棋元.ESG与信息披露制度研究综述[J].合作经济与科技,2024(6):145-14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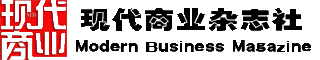


 我国汽运中间品的
我国汽运中间品的 中小外贸企业跨国
中小外贸企业跨国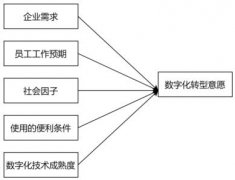 国际货运代理接受
国际货运代理接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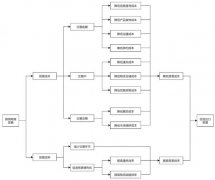 跨境电商发展水平
跨境电商发展水平 “一带一路”视角
“一带一路”视角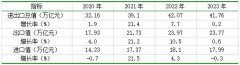 跨境电商背景下贸
跨境电商背景下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