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扶贫对贫困家庭消费的影响
|
——基于CHFS的实证研究 吴诗慧 武汉轻工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本文基于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运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评估了产业扶贫对贫困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扶贫政策显著提高了贫困户家庭的消费水平。消费水平能综合地体现家庭经济福利与幸福感,因此,我国今后的扶贫应关注贫困户的消费这一指标,并积极发展当地特色产业,降低产业扶贫门槛,有利于防止老、少、边、穷等弱势群体返贫,缓解相对贫困,使农村经济发展健康稳定。关键词:产业扶贫;家庭消费;PSM-DID 一、引言
减少和消除贫困一直以来都是全球大多数国家和机构长期致力实现的目标。2020年,中国实现全面脱贫,国家的扶贫事业迈向新台阶。随着“后扶贫时代”的到来,检验和稳固中国现有的扶贫成果成为当务之急。精准扶贫的顶层设计于2013年年末正式提出。产业扶贫是精准扶贫中的一项重要措施,中央政府坚持把产业扶贫作为破解农村贫困问题的根本之策。产业扶贫通过解决贫困居民的就业问题,对贫困户的资本积累、生活方式产生影响。当前我国贫困人口全面脱贫,这得益于产业扶贫兼具推动脱贫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双重功能。 二、文献综述
关于贫困的本质、成因以及治理问题,西方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经典体系,其中影响较大的包括:贫困经济学理论[2]、可行能力理论[3]、发展主义理论[4]、二元经济理论[5]。 中国的扶贫历程充分借鉴了西方的理论思想,形成了一套极具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组合拳”,即精准扶贫,包括精准识别、精准实施、精准评估,具体内容有“两不愁三保障”、“六个精准”、“五个一批”、“六项扶贫行动”、“十项精准扶贫工程”。其中产业扶贫既能大规模实现贫困户就业脱贫,还能持续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具有其他政策所没有的“造血”功能。目前关于产业扶贫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产业扶贫中,省、县、乡级党委政府、村干部和贫困户这五类利益相关主体之间存在摩擦:县级政府的资源分配不平衡,政府在产业扶贫政策自上而下的无差别执行中缺少贫困户的积极参与,贫困户在外出打工的低风险、快回报和参与当地产业政策的高风险、慢回报中两者的选择不言而喻,各级政府在刚性的政绩考核压力下做出的数据造假和串谋现象,村干部工作的“钱少事多”,以及村干部的政府代理人和村庄当家人这一双重身份参在摩擦[7],均使得产业扶贫的效率存在提升空间;有的学者认为产业扶贫依赖科层制实现组织动员与资源配置[8],而另一种观点认为精准扶贫的首要特征在于逆科层化,工作职能的分担打破了常规部门的划分[9]。 第二,产业扶贫的融资模式:当前有学者提出“政银企十N”资产收益扶贫模式,该模式有效捆绑了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和贫困户之间的利益,转变了政府的主导地位,提高了银行、企业和贫困户的参与度,降低了贫困户的高风险[10],但在具体实践中产业扶贫模式差异较大等。 第三,产业扶贫的现实困境:部分贫困地区由于青壮年外出打工的比例不断攀升,从而导致本地劳动力不足、产业凋敝和集体行动能力弱化[11],针对这一问题,有学者研究认为产业扶贫使贫困户的生计模式向农业转移,减少了其外出务工的时间,减贫效果大大的折扣[12],但有效抑制了贫困户的生计脆弱性,究其原因是生计模式和致富意愿带来的影响[13];另外,对于农村留守妇女与儿童的问题,扶贫车间这一方式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有效吸纳贫困女性就业,缓解了农村性别结构性贫困问题[14];其次,政府长期大的输血式扶贫在该地形成了各种利益群体,阻碍了产业扶贫策略转型升级[11]。 第四,产业扶贫的政策效果评估:首先大规模的产业扶持引发了同质竞争、产能过剩、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15];产业投入的低效反而限制了贫困户从中获利,导致产业扶贫项目的失败[16];另外,也有学者认为产业扶贫政策对贫困户的社交具有良性促进作用[17];在产业扶贫政策中,“授渔”的方式给贫困户带来的福利效应增加优于“授鱼”[1]。 通过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发现,以往学者们都是通过收入判断贫困户的贫困状况,但这样的指标评价脱贫与否有时并不精准。消费水平更体现了贫困户对于收入的支配能力[18]。根据需求层次理论,人们通常优先满足生存型的消费需求,其次是追求更高质量的发展。基于“流动性约束“理论,贫困户的跨期平滑消费能力差,即便贫困户的收入增加了,但由于贫困户的长期收入不稳定,其消费水平依然很低。产业扶贫对贫困户的作用机制有两点:第一是提高家庭收入;第二是降低家庭遇到的风险[6]。消费水平能综合地体现家庭经济福利与幸福感[19],因此本文用消费用来评价产业扶贫政策对贫困户的物质生活水平的影响更有效。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金融数据调查2015年和2017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研究。该数据于其他数据库不同的一点在于其中一条具体问到了“您的家庭是否为贫困户?”,为文本对产业扶贫政策的评估提供了数据支撑。2013年年底我国产业扶贫顶层设计投入实施,考虑到政策效果存在时滞效应,本文将2015年作为政策前,2017年作为政策后。 (二)模型设定 通过比较产业扶贫政策前后贫困户消费状况的差别,以评估政策的影响。考虑到人们的消费水平提升并不仅仅取决于政策的实施,也取决其他因素,为了剔除内生性对实证结果的干扰,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模型设定如下:  (三)变量的定义
本文的核心变量为家庭人均消费水平。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控制变量选取了户主的特征和家庭特征[6]。
表 2 变量的定义
(四)描述性统计
表3给出了变量描述性统计的结果,数据表明,较于控制组,处理组样本中整体消费水平较低,户主年龄较大,受教育年限较短,家庭不健康成员比例较高,自有住房比例较低,且家庭净资产和家庭总收入均较少。
表 3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分析
(一)实证结果
实证结果见表4,以人均消费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使用简化后的模型进行不含其他控制变量的最小二乘法和控制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估计方法估计。第(1)列不含控制变量,仅包含核心解释变量did,OLS回归后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产业扶贫政策使农村贫困家庭人均消费提高了9.8%,第(2)列在第(1)列的基础上加入了其他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did的回归系数仍然为正,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产业扶贫政策对贫困户的家庭消费水平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前述假设得到验证。
表 4 产业扶贫政策对人均消费的影响
通过上述回归结果可见,产业扶贫对贫困户的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方面: 第一,产业扶贫可以可以增强贫困户的综合能力,这种综合能力有益于贫困户获得更高的收益和更好的生活水平,进而提高其消费水平;第二,产业扶贫带来了较多的就业和创业机遇,能够促进家庭劳动力资源配置优化、降低家庭面临的外部约束;第三,受产业扶贫政策影响的贫困户消费提升,可见政策提升了贫困户的抗风险能力;第四,受产业扶贫政策的贫困户家庭劳动力更丰富,家庭人口负担相对较低,参与产业扶贫可以更好促进增收,从而改善贫困户的生活品质。 (三)产业扶贫对消费扶贫的促进作用 以前的研究多从产品的供给视角出发,提高产品供给的效率,但是贫困户参与市场需要消费者有购买的意愿,产业扶贫才能实现良性循环,二者之间存在联动关系。消费扶贫是中国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构成部分,绝大多数消费者都比较认同消费扶贫的理念,对扶贫产品具有不同程度的溢价支付意愿[20](全世文,2021)。首先,从回归结果可见,对于消费市场而言,有经济实力的消费者增加了;其次,由于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更强,产业扶贫以城市资源撬动、整合、放大了乡村资源,这为构建新型城乡共生关系提供了思路。 五、结论和政策启示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产业扶贫显著提升了贫困户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2)增强产业扶贫与消费扶贫的关联性可以为贫困户的产品谋出路,构建产业扶贫的良性循环。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转变政府在扶贫工作中的角色,有利于减少政府的过度干预对市场造成的扭曲;第二,有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来源于当地的城市化进程,而当地的乡村价值在强烈的城市化冲击下变得脆弱不堪,产业扶贫对贫困地区因地制宜的特点,有助于稳固乡村传统文化,尤其是旅游扶贫,本地特色的传统文化可以成为旅游扶贫的切入点;第三,产业扶贫与消费扶贫均具有“造血“功效,且二者关系密切,例如农产品生产出来以后,需要减少阻碍消费者购买的因素,当前电商扶贫有效地缓解了这一问题,未来仍存在改进的空间;第四,当前我国减贫成效显著,每一个脱贫的居民都会成为消费者,市场空间巨大,也契合了我国正在加速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重大战略部署;第五,继续强化扶贫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整合,增强贫困户在信息不对称中所处的弱势地位;第六创新发展扶贫产业,改变贫困地区经济薄弱的局面,尤其是“三区三洲”这些扶贫的深水区。 参考文献: [1]朱红根.产业扶贫政策的福利效应及模式比较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21(04):83-98. [2]李学术.从创新视角对舒尔茨贫困经济学的再认识[J].中国软科学,2007(07):105-114+146. [3]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4]亓迪,王化起.发展主义理论视角下的减贫策略研究——以新加坡为例[J].社会工作与管理,2018(06):74-79. [5]Lewis, W.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J].Manchester School,1954,(22):139-191. [6]尹志超,郭沛瑶.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家庭消费视角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21,37(04):64-83. [7]陈秋红,粟后发.贫困治理中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多重摩擦和调适——基于广西G村的案例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9(05):72-88. [8]原贺贺.产业扶贫中的基层治理逻辑解读[J].江西社会科学,2021,41(01):215-226. [9]许汉泽,李小云.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产业扶贫的实践困境——对华北李村产业扶贫项目的考察[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1): 9-16. [10]冯子纯.“政银企十N”资产收益扶贫模式运行分析——以牧原生猪养殖产业链为例[J].农村经济,2021(02):68-76. [11]钟凯.“后扶贫时代”深贫地区贫困治理的理论思考——基于四川省贺波洛乡的实证考察[J].农村经济,2020(11):79-86. [12]胡晗,司亚飞,王立剑.产业扶贫政策对贫困户生计策略和收入的影响来自陕西省的经验证据[J].中国农村经济,2018(01):18-39. [13]李玉山,陆远权.产业扶贫政策能降低脱贫农户生计脆弱性吗?——政策效应评估与作用机制分析[J].财经研究,2020(05):63-77. [14]苏海.让扶贫车间在促贫困女性就业中提质增效[N].中国妇女报,2019-08-13(5). [15]汪三贵,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J].贵州社会科学,2015(05):147-150. [16]邢成举.政府贫困治理的多元逻辑与精准扶贫的逻辑弥合[J].农业经济问题,2020(02):31-39. [17]王振振,王立剑.精准扶贫可以提升农村贫困户可持续生计吗?——基于陕西省70个县(区)的调查[J].农业经济问题,2019(04):71-87. [18]徐月宾,刘凤芹,张秀兰.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反思——从社会救助向社会保护转变[J].中国社会科学,2007(03):40-53+203-204. [19]Jorgenson, D.W.,1998,“Did We Lose the War on Poverty?”,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2(1):79-96. [20]全世文.消费扶贫:渠道化还是标签化?[J].中国农村经济,2021(03):24-45.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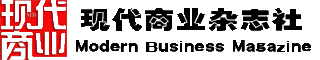


 异质性FDI对我国
异质性FDI对我国 基于网络评论的菲
基于网络评论的菲 四川省竹产业发展
四川省竹产业发展 产业扶贫对贫困家
产业扶贫对贫困家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 数字时代下社区养
数字时代下社区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