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院冻结中国跨境电商企业资金的风险应对
|
覃斌武 湘潭大学法学院 基金项目:2018湖南省教育厅《美国司法权域外扩张对策研究》(134738)。 摘要:我国跨境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给大量中国跨境电商企业带来巨大的收益,随之而来包括境外诉讼在内的风险。其中美国法院冻结资金禁令对中国跨境电商企业造成了明显的风险和损失。2015年以来,美国法院受理的针对中国跨境电商企业的侵权案件超过6000件,中国企业被冻结了超过百亿美元的资金。美国法院随意的和流程式的批准冻结资金禁令,有滥用法院自由裁量权之嫌疑。采取适当的策略积极主动应诉,是化解资金冻结风险,维护中国跨境电商企业合法权益的有效策略。 关键词:跨境电商;管辖权;资金冻结禁令;临时禁令;初步禁令 近年来,跨境电子商务成为我国外贸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国务院批准设立首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截至2022年2月共设立了132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①。跨境电子商务贸易总额从2010年的1.1万亿人民币增长到2020年的12.5万亿元人民币②。大量中国跨境电子商务企业(以下简称“中国电商企业”)入驻亚马逊、Ebay等外国电子商务平台,获得超过千亿的销售收入;中国电商企业也逐渐被一批美国律所盯上,成为其滥用美国诉讼程序收割资金的目标。从2015年开始美国法院出现大量以中国跨境电商企业为被告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其中90%以上为商标侵权案),案件数量每年超6000件。以Greer Burns & Crain LLP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GBC律所”)为代表的美国律所疯狂起诉中国电商。据该律所自己公布的数据,2020年初至今GBC律所已经起诉了8万余家电商企业,其中绝大多数为中国电商企业,两年多时间律所实现营业收入超30亿美元。 美国法院会应美国原告的请求发布临时禁令(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和初步禁令(Preliminary Injunction),命令亚马逊、贝宝(即Paypal公司,提供类似于我国的支付宝服务)等美国公司冻结中国电商企业的资金,导致中国电商企业无法主张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即中国法院管辖),被迫赴美客场应诉,或者选择直接放弃资金和网店——经营较长时间的网店的商誉也随之放弃。法院禁令是美国原告制约中国企业的杀手锏,也是美国法院扩张其域外司法权的武器。一部分中国企业通过积极应诉,成功维护了自身的权益。中国企业可以向美国法院提出无管辖权,可以提出电子邮件送达违反《海牙送达公约》,也可以申请美国法院解除冻结资金禁令,实践证明出庭应诉效果良好。通过对中国电商企业出庭应诉的经验的总结,可以提出应对美国法院冻结资金禁令的策略。 一、美国法院冻结中国电商企业资金的商业背景和规则背景 在美国法院出现的大量起诉中国电商企业的现象,背后有自洽的商业和规则背景。即便无法到中国法院申请执行,美国原告也可以通过大量诉讼获得超额赔偿金——即中国企业暂存在美国亚马逊、贝宝公司的销售资金。 从商业角度,跨境电子商务的经营模式使得中国电商企业随时都有部分资金被美国企业控制,而美国企业又必须接受美国法院的管辖。美国电商平台的结算规则下,中国电商企业的网店账户随时会有部分资金。入驻美国亚马逊的网店,其存放在网店账户的销售金额不能每天提款到自身银行账户,而是每两周才能提款一次③。因此,中国电商企业的网店账户总有数千甚至数万美元资金。一旦美国法院发布临时禁令或者初步禁令,美国亚马逊公司会按照禁令指示,冻结网店账户资金。 既然入驻美国电商平台会受美国法院的管辖,那么选择开设独立站是否能够规避美国法院管辖呢?实践证明开设独立站并不能规避美国法院的管辖。面向美国消费者开展跨境电子商务销售活动,也必须使用贝宝等支付工具才能够收取资金。中电商企业申请贝宝公司服务,必须同意留存特定比例的资金在贝宝账户,还必须同意从客户付款到网店提取资金的留置期。因此,即便中国电商企业不入驻美国电商平台,仍然会面临部分资金被美国企业所控制的情形。 从法律角度,美国法下的禁令制度和对抗制模式使得美国法院可以轻易冻结中国电商企业的资金,而且冻结资金对美国原告于诉讼策略上非常有利。第一,临时禁令无需听取被申请人意见;初步禁令虽然需听取被申请人意见,但现实中我国跨境电商企业往往放弃发表意见或者没有机会发表意见。美国法允许法院根据需要颁布临时禁令,临时禁令的内容可以包括冻结账户。发布临时禁令无需征求被冻结者(被告)的意见,法院审查时仅听取原告的陈述——这是临时禁令的临时性所决定。临时禁令最多冻结账户28条,但是美国原告会在28天期限届满之前申请初步禁令,初步禁令的效力延续到诉讼终结。美国原告在申请初步禁令送达听证通知时往往留给中国跨境电商企业的时间特别短,客观上剥夺了其发表意见的机会。如水气球产品侵权案(伊利诺伊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案号21-CV-2180)中,原告于2021年5月27日(临时禁令有效期的最后一天)申请初步禁令;初步禁令的动议听证日6月2日,但原告直至5月31日才将起诉状、传票、临时禁令、初步听证通知发送给138家被告,因此,即使非常勤勉的被告也不能出席初步禁令听证。所以,虽然制度上法庭应当通知被申请人,而且听取被申请人的意见,但是现实中法庭完全沿用了临时禁令的内容,只是转化为初步禁令之后,禁令的有效期不再是短暂的十四天,而是直到诉讼终结——这对中国电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难。 第二,美国民事诉讼对抗制模式使得法院不会主动质疑原告的主张,而是应该由被告提出异议,否则法院会对原告的诉求照单全收。作为一种普遍的操作模式,美国原告在起诉中国电商企业知识产权侵权时,往往在同一个案件中起诉上百家中国企业。不同的中国电商企业彼此之间并不认识,更谈不上合作。此情景下批量合并是违反美国诉讼规则的;但由于绝大多数案件中绝大多数中国企业不会出庭提出异议,因此美国法官基本上会默许批量合并被告。虽然大多数中国跨境电商企业被告被冻结的资金不到一万美元,但是每次起诉上百家被告,美国原告可实际获赔百万美元以上④。因此,美国的法律规则和运作模式也导致起诉中国跨境电商企业有利可图,这也是近年来美国法院起诉中国企业被告的案件数量飙升的原因。 二、美国法临时禁令和初步禁令的规则 按照美国法美国法院有权命令任何主体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被称为禁制令(Injunction)。禁制令可以分为永久禁制令和临时禁制令。永久禁制令属于实体裁判的内容,是一种判决形式。临时禁制令一般在诉讼进程中采用,与最终的实体判决结果无关,属于临时措施。 临时禁制令可以分为临时禁令和初步禁令,与我国民事诉讼法下的诉讼保全措施颇为相似。临时禁令是由一方当事人申请并由美国法院作出的,为防止对方当事人为某种特定行为而对其采取的临时性的限制措施,其目的在于确保后续判决能够得到执行或确保当事人的利益不受损害。临时禁令的特点是可以单方面申请,法院可以仅依据申请人的主张做出决定,但是临时禁令有效期较短。初步禁令也是法院为确保后续判决可以得到执行而对当事人或者其他人员做出的临时性的限制措施,如冻结资产、冻结账户、冻结网店禁止运营等。初步禁令与临时禁令的区别在于,申请初步禁令必须通知对方当事人和被禁令约束的人,初步禁令的时效较长,一般有效期到诉讼终结为止,但法庭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延长或者缩短。 在联邦法院,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六十五条规定临时禁令和初步禁令。按照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65条第(b)款规定,在满足两个条件的情况下法院可以应申请做出临时禁令:第一,由誓证书(affidavit)或者宣誓的起诉状(verified complaint)证实的事实明显的表明在法庭听取对方意见之前(如果不立即发出临时禁令),“即刻的和不可挽回的(immediate and irreparable)损失将会发生”;且第二,申请人律师书面证实申请人方已经尽力尝试向被禁制人告知申请事项或者法庭不应当要求申请方告知对方的正当理由。需要特别注意,临时禁令申请是在非常紧急的情况,因此,法院可以不征求对方意见即发布临时禁令,故而原则上来说法院会认为申请人及其律师的事实主张为真,仅主张、誓证书、宣誓的起诉状即可,无须确实的证据。申请临时禁制令是当事人的一项程序性权利,当事人必须提供相应的担保,如果措施错误,被采取措施的当事人有权要求赔偿。法庭应该根据可能发生错误申请禁令的情况确定担保的金额,金额应该足以补偿被禁制令限制的人因错误禁制发生的费用和承受的损失。 初步禁令也是一项临时性限制措施,其做出的实质性理由也是为避免给当事人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因此,初步禁令与临时禁令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初步禁令的有效期明显比临时禁令长,必须经过听证程序才能做出。民事诉讼规则第65条第(a)款规定提前通知被申请人是必要条件。初步禁令的时效原则上来说及于整个诉讼过程,不像申请临时禁令更看重事态的紧急性,初步禁令则更看重申请方最终获得胜诉的现实可能性。 申请初步禁令的当事人应当证明三个条件:第一,其有合理的最终胜诉的可能;第二,在该当事人没有足够的法律救济;且第三,如果不发布初步禁令,则该当事人会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害。如果申请初步禁令的当事人不能证明这三项条件,则法院必须驳回初步禁令申请。但即便申请人证明了前述三项条件,法院还要考量禁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以及公共利益;只有在前者大于后两者,法院才能发布初步禁令。 所谓当事人的合理的胜诉可能,是指基于申请时的资料和证据,法庭能够大致判断当事人在后续的诉讼中具有相当程度的机会胜诉。这个标准不要求法庭能够确信申请人一定能够胜诉,而是合理的可能性即可。用不太恰当的百分比表示,不要求申请人有超过70%的胜诉机会,只要超过一半的胜诉机会甚至比一半胜诉机会低都可以。只不过在胜诉机会低于50%的时候,法庭对不可挽回的损害等其他因素的考量将趋于严格。法庭作出的判断并非是对核心实体事实的最终判断,而是一个初步判断。随着案件的进展,法庭并非一定要固守自己在最开始时的初步判断。 在分析不可挽回的损害与法律救济不足的时候,很多法庭将两项要素放在一起分析。所谓不可挽回的损害是一项事实判断,是指如果法庭不给予临时禁令或者初步禁令,即便事后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其诉求,也不能防止损害发生或者赔偿可以完全救济损害,则存在不可挽回的损害。而所谓法律救济不足,是指法律上的赔偿不能完全救济损害。 在专利和著作权侵权案件中,美国法院判例明确指出不能直接推定不可挽回的损害。第三和第九巡回上诉法院认定商标侵权案中也不能直接推定存在不可挽回的损害;其他巡回上诉法院则尚未做出明确的判例⑤。 三、应对美国法院冻结资金禁令的策略 在本类型诉讼中,对我国跨境电子商务企业相当不利的情形是诉讼程序前期的“单方性”,一是临时禁令动议的审查是单方的,二是其他各种程序只要被告不出庭应诉法庭都会流程式的接纳原告的主张。即便如此,并不能指责法庭裁判错误,因为诉讼程序保障公平的“机会”而不直接实现正义。所以我国跨境电商企业应对美国法院冻结资金禁令的第一项策略就是积极应诉,挑战法庭发布禁令的正当性。 第一,我国跨境电商企业可以挑战原告送达初步禁令听证通知的迟延。不同于临时禁令可单方申请,初步禁令申请必须通知被申请人。作为惯常流程,本类型诉讼的原告在获得临时禁令之后首先是向亚马逊、贝宝等机构送达禁令,避免被告转移财产。现实中往往会出现原告送达初步禁令听证通知特别晚的情形,因为一则需要送达的被告很多,二则原告不希望太早送达通知给被告以免被告出席听证反对。听证通知送达和通知日期的间隔如此之短,明显对被告不公平。初步禁令听证通知送达过分迟延是事后挑战法庭发布初步禁令的有力理由,至少能给法庭施加压力。对于应该提前多少天送达通知,美国法院目前并无明确判例,但是如果能找到某个中国被告收到听证通知在听证日之后的,也许可以创设对中国电商企业有利的先例判决。 第二,我国跨境电商企业可以挑战原告的事实主张。大多数的原告律师事务所在大多数的情形中会重复使用相同的诉讼文书模板。文书模板的重复使用导致事实陈述的两个问题:第一事实陈述空泛,不带任何细节;第二,多份不同案件的书状事实主张完全一样。美国民事诉讼法下,在起诉阶段和禁令申请阶段,原则上法庭应当接受原告主张的事实为真,并不要求较高的证明。但是如果原告的主张全然是结论和推断,则法庭可以不接受原告的事实主张。原告往往会空泛主张“被告的侵权行为损害了原告的商誉”、“被告的侵权行为导致消费者对原告产品质量信任的下降”等,但是按照雅诗兰黛案、Klipsch案等判例确定的规则,这样毫无细节事实的主张仅构成结论和推断,法庭可以不接受⑥。我国企业在应诉时应该着重强调,原告诉讼文件与其他案件中的诉讼文件表达高度雷同,说明原告事实主张空泛并且原告律师事实调查不勤勉。如果原告不能证明不可挽回的损害,那么法庭自然就不应当发布禁令,如果已经发布禁令的,应当按照被告的请求解除禁令。 第三,在具体事实对个别被告有利时,作为被告的中国企业应当主动提供相应证据和声明(类似书面证言)争取法庭解除冻结。原告律师识别潜在的被告往往采用网络技术抓取数据,不会仔细审核每个被告的侵权事实,因此每个案件中总有一部分被告是被“误伤”的。这些被告可以在提交解除禁令动议时附上相应的销售数据和声明,证明自身根本没有任何侵权行为,从而要求法庭解除禁令。即便存在侵权嫌疑的被告,也可能存在有利事实,如虽然侵权但是并未销售到法庭所在州(因此法院无管辖权);或者虽然侵权,但是侵权产品销售金额很低等(因此无需冻结被告资金)。这些有利事实,能够说服法庭支持被告解除禁令的动议。 第四,我国跨境电子商务企业被告如果是小微型企业,则可以向法庭主张禁令给企业的经营以及员工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个主张可以通过声明的方式去证实,而主张的效果则在于可以有力驳斥发布禁令给被告造成的损害较小的主张,因此可以支持基于利益平衡的考量,也应该解除禁令。 我国跨境电商企业应对美国法院冻结资金禁令的第二项策略将明显降低冻结金额作为战略目标。首先,法庭完全解除禁令的概率并不大。大多数被告是我国企业且在美国没有财产,一旦解除禁令我国企业转移财产非常合乎情理,因此美国法庭不太可能直接完全解除禁令,合理的策略是以前述理由给法官施加压力,迫使法庭确定较低的冻结金额。 我国跨境电商企业要求法庭确定较低冻结金额的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初步禁令冻结资金仅能基于原告胜诉后获得实际损失之目的,不能基于原告获得法定赔偿或者惩罚性赔偿之目的;冻结资金的金额应该与被告的所谓侵权行为相匹配,并且法庭应当考虑要求原告提供担保与冻结被告资金的适度公平。原告的常见策略是在起诉时主张任何可能的赔偿。由于美国商标法和版权法规定了较高的法定赔偿标准,因此被告总会主张法定赔偿。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流氓律师事务所并不打算在美国法院判决之后到中国法院申请执行,其目标仅是中国被告被冻结的亚马逊、贝宝账户的资金。一旦被告申请法院修改禁令降低冻结金额,美国原告肯定会以法定赔偿的最高限额为依据提出反对;但是美国原告的这项主张是不符合美国判例法规则。联邦最高法院有判例明确表示,禁令作为一种衡平法的救济手段,只能与原告主张的最终的救济相适应。 第二,法院禁令冻结的被告资金应该与被告的所谓侵权行为相匹配。如果我国跨境电商企业没有侵权、侵权销售额不大、侵权程度很弱,则应以事实为依据,主动要求法院降低冻结金额。在美国法下,商标侵权案的实际损失赔偿确定基准并非销售额而是非法获得的利润。因此,法院更有理由确定一个较低的冻结金额。此外,法庭还应当考虑初步禁令发布仅是一种临时的、初步的判断,不影响案件的最终结果。即使法庭发布了初步禁令,后续诉讼中原告败诉的案件也比比皆是。因此法庭考量冻结被告的资金金额时,应当在原被告之间适度平衡。法院不应该裁决原告申请禁令,仅需提供一万美元担保;而被告则要被冻结十万美元的资金以供未来“可能”的判决执行。 如果中国企业被告销售所谓侵权产品数量很大,从诉讼策略角度,仍应提交解除禁令申请。这是因为美国律师习惯挣快钱,根本无心进行实质性的法律辩论交锋,因此,被告提出动议是一项争取有利和解的筹码。比如在伊利诺伊北区地区法院审理的KTM a.g.案和Entertainment One UK案中,原告律师根本无心提交法律备忘录答复被告的动议,而是在两次申请延期后与被告和解。虽然我们无从得知和解的条款,但是考虑到是原告律师未能提交法律备忘录,理论上和解应该对中国电商企业被告比较有利。 总之,中国企业应对美国法院冻结资金禁令的第一策略是积极应诉,第二项策略则是以法院明显降低冻结金额为目标。一旦法院明显降低冻结金额,则被告一可以重获大部分资金,二则被告能够以降低后的冻结金额为基准与美国原告谈判和解。 四、结语 美国民事诉讼法下的临时禁令和初步禁令是一种非常规的衡平法的救济手段。临时禁令制度对我国跨境电商企业非常不利。在临时禁令是单方面申请,初步禁令由临时禁令转化而来的情况下,美国法院往往更倾向于支持原告发布禁令,这对我国跨境电商企业非常不公平。虽然可能存在一部分被告实施了侵权行为,但不代表全部被告都有侵权行为;即便实施了侵权行为,也不一定应当向原告赔偿其主张的金额。因此,我国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应该积极应诉维护自身权益。 同一宗诉讼中,不同被告的情况可能存在明显差异,原告在起诉状和禁令动议中的事实主张对部分被告而言往往不实,因此被告应该结合自身的情况,向法庭主张有利于己的事实,争取法庭解除禁令或者明显降低冻结金额。从诉讼策略来说,如果法庭同意明显降低冻结金额,则被告可以迫使美国原告和解。 注释: ①国务院关于同意在鄂尔多斯等27个城市和地区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国函[2022]8号,2022年2月8日。 ②谭芬,侯瑞瑞.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对进出口贸易的提振效应考察——基于美日欧样本数据的比较[J].商业经济研究. 2022(4) 161-164. ③江义火, 袁晓建, 吴昌钱. 中小零售企业B2C跨境电商平台选择策略[J]. 商业经济研究. 2019(19) 78-81. ④雅诗兰黛案,Estée Lauder Cosmetics Ltd. v. Partnerships and Unincorporated Association Identified on Schedule A, 334 F.R.D. 182 (2020). 该案亚裔法官Edmond Chang对于在没有证据证明被告的关联情况下合并大量被告的现象表示了担忧。⑤⑤See Ferring Pharm., Inc. v. Watson Pharm., Inc., 765 F.3d 205, 217 (3d Cir. 2014); See also Herb Reed Enters., LLC v. Fla. Entm't Mgmt., Inc., 736 F.3d 1239, 1249 (9th Cir. 2013). ⑥Klipsch Grp., Inc. v. Big Box Store Ltd., 2012 U.S. Dist. LEXIS 153137, at *20 (S.D.N.Y. Oct. 24, 2012) 参考文献: [1]谭芬,侯瑞瑞.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对进出口贸易的提振效应考察——基于美日欧样本数据的比较[J].商业经济研究,2022(04):161-164. [2]江义火,袁晓建,吴昌钱.中小零售企业B2C跨境电商平台选择策略[J].商业经济研究,2019(19):78-81. [3]Estée Lauder Cosmetics Ltd. v. Partnerships and Unincorporated Association Identified on Schedule A, 334 F.R.D. 182 (2020). [4]Ferring Pharm., Inc. v. Watson Pharm., Inc., 765 F.3d 205, 217 (3d Cir. 2014); See also Herb Reed Enters., LLC v. Fla. Entm't Mgmt., Inc., 736 F.3d 1239, 1249 (9th Cir. 2013). [5]Klipsch Grp., Inc. v. Big Box Store Ltd., 2012 U.S. Dist. LEXIS 153137, at *20 (S.D.N.Y. Oct. 24, 201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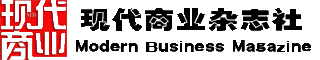


 RCEP框架下我国跨
RCEP框架下我国跨 我国跨境电商产业
我国跨境电商产业 农村电子商务支持
农村电子商务支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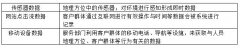 基于大数据时代下
基于大数据时代下 我国西部电子商务
我国西部电子商务 基于招聘网站的电
基于招聘网站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