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定解除认定的理论要件和实务标准研究
|
李学勇 潍坊职业学院 摘要:本文对合同法定解除权进行研究,指出合同法定解除制度在理论中的争论焦点,结合司法案例实践梳理细节,发现合同法定解除权在理论要件和实务标准间关注点的差异性,理论争论焦点没能反映在实务判决中,而司法实践更关注制度细节,对法定解除权的适用更谨慎。 关键词:合同法;理论要件;实务标准 合同法定解除是在合同有效成立后,出现法定情形,一方行使合同解除权,使合同关系归于消灭的情形。较之双方合意解除合同而言,合同法定解除只需要一方当事人意思表示即可,与合意解除不同,法定需要有法定解除事由。在《合同法》第94条中对“法定解除权”进行了清晰定位:“合同终止-合同解除-单方行使解除权-法定解除”。本文试图从合同法定解除权的理论和实务的制度理解进行比较,发现二者的关注侧重点与关联。 一、违约法定解除的理论争议焦点 合法法定解除权理论争议是一个重要问题。根本违约制度的本质是信赖利益理论的基础,是在动静态平衡安全之上,第三人相信法律行为是有效的,但会因某个特定情形,导致法律行为无法正常有效,造成实际财产利益和缔约机会的损失。在合同中一旦这种信任被破坏了,合作就会塌方。信任作为合同的一项前提,如果一方不信守诺言行为,违背合同中双方的约定,必然需要通过解除权对信赖予以矫正。 从合同法定解除权角度看,需要考虑法定解除权的适用合同种类,如债权合同、双务合同、一次性的合同;物权合同没有讨论的必要,单务合同没有制度保障必要;继续性合同的法定解除权在实际法律条款中是有肯定存在条款的。具体的合同法定解除事由中,包括因违约行为导致的合同解除和因不可抗力等客观因素导致的解除权,如拒绝履行而发生的解除权、因迟延履行而发生的解除权、不能履行的解除权、因不完全履行而发生的解除权、不安抗辩权引起的解除权、附随义务的违反而发生的解除权、债权人迟延的解除权。 通过对因违约行为引起法定解除权的归纳,也并非一旦违约就解除合同。从违约严重程度、违约要求违反的是“主要债务”以及违约方是否存在“根本违约”解除原因。只有当合同违约达到一定程度后,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才能动用合同解除权;违约要求违反了“主要债务”,考虑合同目的与义务、附随义务无法实现,即从义务、附随义务的违反一般不能导致合同解除;《合同法》第110条款,“事实上不能履行”,合同判决消灭。 合同解除权是一种形成权,是不需要对方当事人同意的,只需要一方意思表示即可解除合同,只需要通知相对方即可。合同解除权是一种只需向对方意思表示,即产生法律效力的法律行为。在对方有异议时,需要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合同解除效力,据此法院做出确认诉讼。 二、司法实务的裁判标准 以司法案例对合同解除案由进行说明,界定司法实务中合同法定解除权的情形。 (一)合同解除认定情形 1、人身属性成为“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一个标准 《合同法》第94条款中明确法定解除事由的几种情形,在后半部分规定其他违约行为致使无法实现合同目的情形。在司法实务中需要对哪些违约行为导致无法实现合同目的进行明确。如,在租赁合同中,涉及合同双方的人身属性,将构成违约,导致对合同目的实现具有实质性负面影响,构成法定解除权前提条件,具有解除事由。 2、诉讼中的双方约定解除不能否定法定解除事由 合同中一方违约在先,非违约方向法院提请诉讼,确认双方合同解除,在诉讼中违约方同意解除合同,法院对合同解除具有确认作用,即确认之诉。在诉讼前,合同双方已满足法定解除的条件,确认合同解除,和诉讼中合同双方是否达成协议解除无关(后者仅系实务处理)。 3、对于合同成立但未生效的解除权认可 在《合同法》的司法解释规定中,表示双方发生纠纷后,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可以确认合同解除。但是,在司法实务中,明确提出允许合同解除的情形占少数。司法实务中没有对合同成立但未生效的解除权认可进行明确表态,在判决赔偿时,认定合同未生效和合同解除效果相接近,在很多司法案例中均有体现。 4、以违约为事由的法定解除权 在司法案例中,涉及诉讼法定解除的合同案例中,因违约而起的案例占多数,与违约相联系的主要有违约的损害赔偿和合同解除后果。法院在诉讼中需要判断因违约发生是否导致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因此,法院非常谨慎对待因合同违约导致合同解除权是否具备前提条件。 (二)合同未解除认定情形 1、合同法定解除权行使须经催告 合同法立法理论认为合同解除时间是比较明确的,需要解除权人通知另一方,在某些情况下(如一方迟延履行)要求必须经过催告才能行使合同法定解除权。但是,从司法实务看,合同法定解除时间并没有明确无疑义。在实务中,合同解除时间常有争议,合同法定解除权行使必须经过催告,甚至需要以被告的回函时间作为被告收到解除催告的时间。 2、合同履行完毕则无法主张解除权 合同解除制度用于救济成立且有效的合同约束,即合同未完成履行的情况。法院对合同是否完全履行具有自我裁量的权限。从司法实务可以得出:理论界定和法条看似完整准确,但是在实际裁判中却遇到模糊地带,法院在判决“是否实现合同目的”时,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3、非违约方的行为需考虑是否成立法定解除权 法院对迟延履行、附随义务不履行是否成立根本违约中,非违约方是否享有解除权是比较谨慎的。法院会权衡违约责任对合同履行的损失以及合同解除后的赔偿损失,提出折中方案解决合同是否存续的问题。 (三)司法实务中合同解除的裁判思维 通过对司法实务的分析,比较合同法定解除理论要件和实务标准的不同关注点,分述如下:第一,司法实务更关注制度细节。制度细节成为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争议点,如合同解除时间问题,在司法实务中,法定解除权行使中是否需要以另一方催告时间为准,对事前约定不经通知另一方即可自行解除,事前约定更改解除权行使程序等问题存在质疑;第二,理论争议焦点未反映于实务判决。在司法裁判中,具体裁判结果不会受某学说理论限制,而是借助某理论更好理解某法条;第三,司法实务中对法定解除权的适用更谨慎。法院裁判更侧重于考虑合同解除后果,采取退让性策略,通过法定解除诉讼的退让确认,获得最优化裁判结果;第四,司法实务十分关注解除权人是否提出诉讼,法院是否有权裁定合同解除效力等问题。即,当合同解除权人解除合同后,另一方存在异议,有权向法院提出诉讼,确认合同解除效力。法院比较关注解除权人可否通过法院行使解除权,是法院干预合同解除的入口。法院认为解决纠纷的关键点在于区分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但是需要明白的是私力救济的同时并不排斥行使公力救济,基本法理站得住脚;第五,把握合同解除权消灭事由的实际范围。在期间届满、未行使催告、不能返还受领标的物、受领标的物种类变更等情形予以认定合同解除权。对合同解除权的抛弃消灭理由的一般性,无法特别规定。 通过对合同法定解除理论要件和实务标准的双重考察,发现实务标准对制度细节更关注,理论要件中争论焦点没有反映在实务标准中,司法实务对法定解除权适用问题很谨慎,司法实务更关注法院是否有权裁定合同解除效力,解除权人能否提出诉讼问题。合同解除权的消灭事由具有自我把握范围的特点。 参考文献: [1]王勇.合同法定解除的法律后果分析[J].法制博览,2016,31:176. [2]潘振华.试论合同法定解除权的原因、程序和方式[J].当代经济,2015,33:92-93. [3]欧超荣,叶知年.论合同法定解除与恢复原状[J].理论界,2015,03:55-6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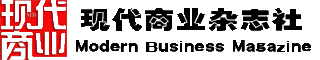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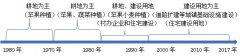 村改居背景下农村
村改居背景下农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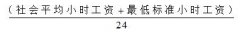 “时间银行”模式
“时间银行”模式 老龄化背景下医药
老龄化背景下医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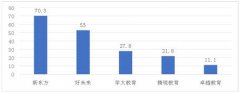 浅谈中国K12教育
浅谈中国K12教育 新媒体与产品代言
新媒体与产品代言 高校周边健身房大
高校周边健身房大